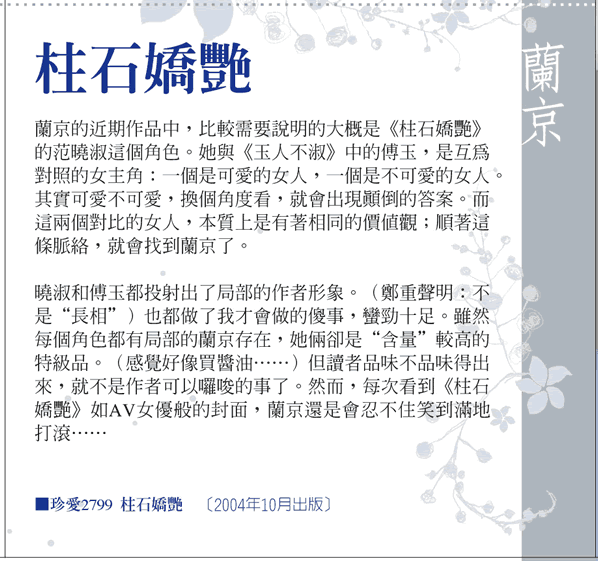[1 ][2 ][3 ][4 ][5 ][6 ]
作家精選回顧--
蘭京座談會
芃羽專訪
蔡小雀專訪
決明專訪
凌淑芬專訪
可兒專訪
季璃專訪
綠痕專訪
夏娃專訪
憐憐專訪
葉霓專訪
連亞麗專訪
黑潔明專訪
四月專訪
蘭京專訪
嘉恩專訪
娃娃專訪
舒格專訪
編: 妳可以的。〔滿滿的愛呀〕蘭: 我們等等再來談這一本書好了,說妳受了多大的災難。〔笑〕
另外一個掙扎就是,我不喜歡我的女主角,我也不喜歡我的男主角,他們的個性。我欣賞他們的長處,可是,有一些與我價值觀衝突的部分,我不能接受,我卻要說他們的故事,用他們來說故事,因為我剛才說了,我不能改變一個「人類」,我可以改變「故事」的架構,所以有一些男女主角沒有遵守婚前不應有性行為的規範,那是因為他們的價值觀已經被扭曲了,我很想把它調整回來,讓他們變成是在感情上面可以專一,在感情上面去發揮永恆的聯結。座談會後的蘭京補述:我在〈蘭京專訪〉中曾提過,我必須要先去喜歡那個角色,然後才去書寫他們。在這段回應中,我對男女主角的感情經營方式卻回以「不喜歡」,似乎與專訪中的言論衝突。 (座談會後的蘭京補述:為求慎重,蘭京還是別隨便用vision這個字的好。因為它不是以自我為中心所定的標準,它的源頭、過程、目標,都不同於市場利益導向的操作。我可以說我以vision這樣的「心志」來看待自己在言情小說界的奮鬥,但不表示我就可以擅自把這個稱之為vision。特此釐清。) 雖然言情小說這個類型被放在(二館)這樣的場合──你就知道在整個出版品裡它的定位在哪裡,但是你可以把自己定位成你是在一館的人,你是在一館聽這樣的座談會。〔自信〕座談會後的蘭京補述:以下的一段談話,周遭音效非常吵雜,加上間隔性的收音斷訊,難以完整記錄。而且事隔一個多月,蘭京在當場到底講了什麼、想表達什麼早已忘光光。因此,這題會在文末附錄的〈蘭京獨白〉重新回答。謝謝小編,很辛苦地聽音辨字整理現場收音文字記錄……就當作是蘭京在欺負妳好了,嗚嗚嗚。
袖: 謝謝!蘭京這段回答真的非常非常精采。有想睡覺嗎?沒有,對不對,因為真的非常非常的精采。(蘭京啜泣:謝謝大家。)
(編按:此處主持人應蘭京要求,將三個問題合併一起作答)座談會後的蘭京補述:這個問題可由關先生代答:「我們的婚事背了太多包袱,可是我並不想讓兩家事業的利益,攪進我們之間的關係裡。……就當我對感情有潔癖吧。」(《盤旋之戀》,P.64) 座談會後的蘭京補述:蘭京不是沒寫過平平淡淡的愛情,也不是我不在乎這樣的感情,而是寫了卻沒有多少人在乎,甚至幾乎沒有察覺到那些作品的存在。這是蘭京由讀者來信及一直以來的問題回應中,得到的觀察結果。有兩本書是不同於蘭京其他作品的書寫風格,只是結果很慘,女主角及她的感情完全不得讀者的青睞。即使如此,她們仍是我書寫過程中的寶貝。雖然她們不被消費市場及大眾的口味所肯定,她們仍在我的作品中佔重要地位。甚至那份重要性,會隨著蘭京此後作品的進展具壓倒性的關鍵地位。所以啦,這些女主角來跟我哭訴抱怨的時候,蘭京總得感慨而疼惜地拍肩安慰:不要緊,他們不懂妳,我懂。大家不接受妳,我接受。哎,作者難為……
最後一題是,會不會有一本所謂的大結局?因為在拜讀過程中,會感覺背後似乎有很大的陰謀。蘭京是已經想好所謂的架構跟演進才動筆寫整個系列,還是隨著每個故事推演,在腦海中才慢慢成形,至今也還未完全明朗化?蘭: 不好意思,我一直看錶的原因,是我要根據時間的長短,來決定我這些問題要回答的幅度。
座談會後的蘭京補述:當時為了趕時間,搶在時限之前把問題答完,結果劈哩啪啦拚命講。事後一聽,不禁慘然。真是亂七八糟,不知所云,而且重點在哪也不知道……我果然不太適合現場式的回應。算了,包袱款款,回我的深山繼續當「自在野人」去也!
袖: 我打岔一下,桌面會這麼乾淨(只放著一隻手錶……),是蘭京的要求,並不是我們不尊重主講者而未擺茶水什麼的。蘭: 因為我們時間不多,可是後面的問題我覺得滿重要的,有關情慾的部分,我前面就已經先答過,所以這一題就在那裡結束。後面的問題,我把角色類型化的問題放在最後,我先回答所謂的「大結局」。蘭: 糟了,我有點思想渙散……大架構,對。他們採取解構法作為知識探討及理論進路,但解構的結果並非想從這被拆解的七零八落中,重建任何修正、改良或更真實的理論。所以,尼采宣佈「上帝已死」,否定這賦予意義的主體存在。而傅柯宣佈「作者已死」,更徹底摒棄了客觀意義的存在。因此,後現代主義者認為任何文本都沒有所謂的特定含義,他們可以各隨己意地玩弄或詮釋文本,不需考慮詮釋的正確性,也不需讀出文本的意義。(鄭祥福,後現代主義,2000。 )Federico
de Onis,1934。 ),後來湯恩比也用了這個詞:後現代。可是它要經過了三、四十年的沉澱才成為一種文化現象,到了一九六○年代、一九七○年代的時候,它從一種邊緣文化、進入主流文化,從主流文化再經過,到九○年代之後,成為一種流行文化,它滲入流行文化之後,被廣泛地接納,普及化,就影響到我們日常生活所有的思考。(Grenz,A
Primer on Postmodernism,1996。 )後現代主義的世界觀,正是一種「沒有世界觀」的世界觀,在多元角度跟多元觀點的大前提之下,他們的世界不是一個,而是多個,每個人都在他自己的理解與自己的詮釋中,建構自己的世界。延伸出來的,是各自為「是」:你有你的「是」,我有我的「是」,而且各人的「是」都是不容質疑或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