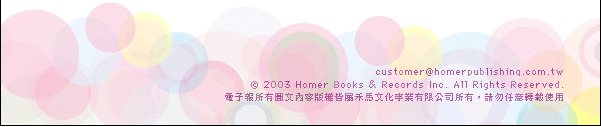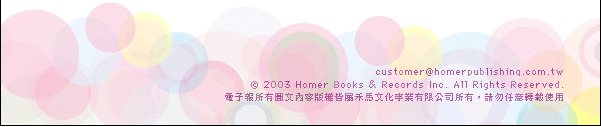|
連載專區:
宇玄《鼎興王朝之逆王狂妃》
☆☆☆ ☆☆☆ ☆☆☆
鼎興王朝,徽慶二十二年。
天邊雲層翻滾,厚厚實實,層層疊疊,彷彿壓在人心頭,沉甸甸的。
快要下雨了。
抬手擦了擦額鬢細細密密的汗珠,握緊了手中韁繩,金令月輕輕嘆了一口氣。
離開京城已經半個月了,不知家中父母怎生掛念,娘親的哮喘可曾發作?爹的傷勢可有反覆?
想起臨行時,娘親拉著她的手,憂心忡忡反覆叮囑,眼中淚光閃閃,金令月心中不禁一痛。
雖然不是第一次出遠門,但獨自一人押鏢還是頭一回,爹娘又怎能放下心來?
她,金令月,威遠鏢局當家金弘義的獨女。
想當年,威遠鏢局聲名遠播,黑白兩道之人看到亮出「威遠鏢局」的旗子,都會賣個面子。
近年來,偌大的鏢局漸漸沒落,生意冷清,父親也年事漸高,膝下又只有一個女兒,沒人接班,因人手不足,父親在護鏢途中受了傷。
為了一家生計,她一個姑娘家才咬牙接下這筆「暗鏢」,改換男裝獨自遠走西戎。
等這趟「紅貨」送到,五百兩的「鏢禮」足夠家裡數年的開銷,爹娘也該好生安養了。
不經意輕按腰間之物,金令月柳眉微蹙,風塵僕僕依然掩蓋不住賽雪肌膚,清秀絕麗的五官流露出一絲焦慮。
山林之間沒法縱馬疾馳,然離客棧還有一程,定要在下雨之前找到地方落腳,不然一場暴雨下來,一身男裝定是掩蓋不住她的女兒身,到時不知會惹來什麼麻煩!
「請留步!」前方傳來一個沉穩的男聲,語調中夾帶著不容抗拒的威嚴,雖非揚聲高喊,卻是確實的傳進對方耳中。
金令月心裡咯登了一下。此處方圓百里並無人家,為了安全起見,她並未走官道,專揀深山密林小道行走,怎麼會有人聲?難道……
她循聲望去,遠處林木間走來修長的身影,那是一個二十開外的年輕男子。
男子一身黑色俠客勁裝襯出他修長的身軀,面容俊美無瑕,一頭如絲絹般的黑髮迎風翻飛,看似溫文爾雅,然而,那雙彷似無垠夜空的黑眸卻深邃晶亮,隱藏著難測,眉宇間極力斂藏著那與生俱來的威嚴。
壓下心頭疑惑,金令月雙手抱拳,沉下聲問道:「這位大哥,請問有何指教?」
她暗忖道:單看這股斂藏不住的尊貴,眉宇間更是充滿了不怒而威的氣勢,就可看出眼前的男子來頭不小!
只是,對方是何人?有何目的?
男子眼中一閃戲謔之色。「嗯哼!此樹是我栽此路是我開,要想過此路,留下買路財!」
遇上劫道的了?不過……這樣的喊話方式,不會是從市井茶社、說書人口中學來的吧?那麼不專業!
看此人出塵的外貌、不凡的氣度,雖極力隱藏那天生的雍容、威嚴的氣勢,但怎麼也不像那些趁火打劫的宵小之徒呀。
但是,人不可貌相!
金令月略一沉吟,低頭下馬,從懷中摸出幾兩碎銀,雙手奉上。「這位大王,小人為探遠親路經此地,請大王行個方便。小小心意,不成敬意。」
男子一陣詫異,好似沒有想到她會那麼容易就掏出銀子。
難道找錯人了?
他對眼前人細細打量一番:清瘦的身型,著月色素袍,歷經長途卻整潔乾淨,背上斜背一個小小的藍布包袱,白皙的肌膚,臉孔俊俏得彷彿不食人間煙火,神情中帶著一絲愁倦與淡然。
淡然?
果然沒找錯人!一個平凡路人若是遇到打劫,會那麼淡然,沒有絲毫惶恐與不安?若是身手不凡的江湖中人,也不會那麼甘心乖乖奉上銀兩消災免事。眼前這人一定就是他要找的「她」!
想到這,男子一雙眼眸精光灼灼,有著剖析人心的銳利。
「遠方探親?為何要違抗繳械令,私帶兵刃呢?趕緊把妳身上的東西交出來吧!小、娘、子。」男子故意試探道,說完還故意瞥了一眼她手中那把長劍。
金令月聞言,心中一驚,倒退一步,緊了緊手中的劍,心想:他怎麼知道她是女的?什麼地方露出了破綻?聽他的意思,像是衝著她懷裡的東西來的,難道是走漏了風聲?
當初那客人是深夜造訪,悄悄議定鏢禮,簽下鏢單,言明此趟貨物甚為貴重需走暗鏢,不能讓外人知曉,家中也只有父母知道這件事情,又怎麼會走漏了消息呢?
想到這,她揚聲用鏢局「唇典」說道:「合吾的朋友,在家日月宮,在外並肩子,吃的是一家的飯,穿的是闔家的衣,把招子放亮了,別崩了盤子,連本帶利折了,給咱托線孫放開一線天。」這話的意思是:道上的朋友,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大家同是江湖人,給個面子,別認錯了人鬧了誤會,賠了夫人又折兵。網開一面給口飯吃。
「唔?」男子怔了怔,而後,幽深似泓潭的眼眸閃爍著洞悉的眸光:「妳說的是什麼方言?我只要妳身上的那件東西,趕緊交出來吧!」
他悠緩地移動腳步向她走去,那威懾迫人的氣勢卻是強烈的擾亂了周遭的氣流,令人不禁屏息。
金令月心中警覺起來。
他果然不是江湖綠林!哪有江湖中人聽不懂「唇典」的?(注:唇典,也叫春典,即江湖常用的行話。)
這一試,對方果然露出了馬腳!
鏘──
金令月抽出手中長劍,直指他的鼻尖。「你不是強盜,也不是江湖中人!你到底是什麼人?有何居心?」
剎那間,雙方的氣氛更加緊繃,那股異常洶湧的對峙已被拉至頂點。
這時,男子伸出一根手指,輕輕推開眼前的長劍,心中暗讚這女子的聰慧過人,捉狹地湊近她的臉孔。
「本大王是誰,妳日後便會知曉,不過我現在的目的可是──財色兼收!」男子邪邪一笑,凝視她的目光犀利如鋒銳。
說著,他轉身躲過刺來的一劍,看到金令月原本雲淡風輕的神情帶上了火氣,有心的繼續調笑:「美人兒,跟本大王回去做押寨夫人吧!」
金令月按捺住心中那一絲不安,反手又「唰唰唰」的連刺三劍。
這登徒子武功不俗!他言語輕佻,卻另懷鬼胎,她遇到大麻煩了!
轉眼間,兩人已交手數十招。
金令月忽覺真氣一滯,胸中血氣翻湧。「你……你下毒?好卑鄙──」怒火攻心,她眼前一黑,昏死過去。
☆☆☆ ☆☆☆ ☆☆☆
彷彿有面大鼓不停的在腦中敲打,綿密如雨的鼓聲在耳畔轟轟作響。
「嗯……」金令月按住像要裂開的頭,濃密的眼睫搧動了幾下。
「娘子,迷香粉的效力已經退了,張開妳那燃著怒焰的眼眸吧,為夫就在妳身邊。」橫臥在床榻上的男子優閒的支著頰,優美的薄唇慵懶勾揚,俊顏上始終綻著別有深意的笑。
金令月緩緩地睜開眼,當她的視線漸漸清晰,面前不足三寸距離前,一雙晶亮的眼睛正看著她。
眼前的男子,那迷離的眸瞳裡流淌著迷惑人心的魔魅,眉宇間卻透出一股與生俱來的王者傲態。
金令月斂下心神,暗忖:這人清俊的臉上帶著一絲壞笑,好像有點眼熟……
勾起她記憶的是他那雙充滿企圖的眼。
「是你!」金令月立刻驚醒過來,揮起一掌就要向他劈去,可全身經脈空蕩蕩的,一口真氣怎麼也提不上來。
「小娘子在內力全失的情況下還想掙扎,可真是深深勾撩了為夫的心,為夫迫不及待地想要品嘗妳這美麗的身子……」男子輕撩起她一縷長髮,並在她髮絲上印下一吻,唇角的笑更加玩味。
驚怒交加的金令月目光凜冽,「你這無恥小人!到底對我下了什麼毒?」
「不是毒,是軟筋散。放心吧,為夫下的分量不多,只不過讓妳一個月裡內力全失而已。」男子迅速伸出大掌,攫住她的下頷,並以拇指摩挲著她柔嫩的唇瓣。
「你有什麼目的?」金令月寒著聲問,語氣夾帶著極度的憤怒。
「我要妳做我的『押寨夫人』!」男子的長指覆在她紅唇上,曖昧地輕撫著,並以貪戀的目光緊鎖著她,像是看著自己的獵物做垂死掙扎。
「你確定要我做『押寨夫人』?」收斂心神後,金令月扔出一個很刻意的問題。
「是的。」男子如鬼魅般的聲音縈繞在她耳畔,字字句句清楚敲進她的心裡。「向來我想要的東西沒有得不到的,倘若妳不答應,那我只好強迫妳了。」
「閣下有此自信是件難得的喜事,但是自信過了頭,就是自大。」話落,金令月迅速出手,從袖裡扯出匕首,抵住對方的頸項。
「就算我內力全失,也可以取你的性命,不知閣下相不相信?」她瞇細了雙眼,挑釁地睨著他,紅唇揚起一抹倨傲的笑。
男子無視於頸間那威脅的力道,似笑非笑地開口:「外面全是為夫的人,小娘子妳說我死後他們會怎麼對付妳呢?或者小娘子可以試一試,在妳內力全失的情況下還能放倒幾個高手?為夫很期待小娘子能激發出自己的潛能,讓為夫開開眼界。」
說著,他趁她不備,攫住她的手腕,並且以威脅的力道按在她手腕的麻穴上,迫使她放開手中的匕首。
自小習武的金令月立即警覺起來。
看來他是有備而來!
男子淡然的輕笑聲竄進她耳裡,似要摧毀她的心理防線,撩撥起她更高熾的怒焰。
「閣下『好心』的提醒還真讓在下受寵若驚,不知閣下到底想怎樣?」金令月也笑了笑,卻是皮笑肉不笑。
男子滿意地看著她收回了手。「為了讓妳安心留在我身邊,使點小手段是必要的。我可捨不得讓妳擔上謀殺親夫的罪名呢!」
「既然捨不得,還麻煩閣下『高抬貴手』,以免在下一顆小小的心承受不住閣下給的『驚喜』而心膽碎裂呀!」金令月扯開緊繃的唇,略帶自嘲的應著。
「好好休息吧,等天亮了,我們還要趕著上路呢。」男子朝她拋去一記挑逗的媚眼,「倘若小娘子想與我同寢而眠,我也樂意為妳效勞。」
「如此的『榮寵』只會讓在下提早歸天,正所謂上天有好生之德,閣下不如給上天一個薄面、做件善事,下輩子閣下也能投個『虎』胎,不必做假的山大王,亦是一件美事。」金令月言詞犀利的回敬。
做個真正的「山大王」也不錯,說白了就是來生投個什麼獸胎,做隻真正的野獸!
「小娘子不必推拒,這份『榮寵』遲早都是妳的,好好期待吧!」說罷,他起身下床,也不等金令月回答,帶上門離開。
身後傳來「砰」的一聲,像是什麼重物砸在已關起的門上。
他臉上笑意又濃了一分。
房中的金令月突然心中一突,伸手摸向腰間,懷中空空如也。
她腦子一炸:完了!東西不見了!
彷彿一盆冰水從頭頂澆下,一時間,她腦海中一片空白。
鏢丟了,功力盡失,人還落在一個登徒子手上。若是誤了客人定下的期限,遠在長安的爹娘失去了她的消息,客人上門問罪,砸了鏢局的名聲不說,光是上萬兩的賠償金,就能把二老壓垮!
接鏢前,她思慮再三才精心定下路線,就是為了防人劫鏢。人算不如天算啊……
可是,在訊息這麼隱蔽的情況下,又怎麼會「洩鏢」的呢?
難道是客人那邊出了什麼意外?
仔細想來,這劫鏢的登徒子並不像江湖中人,可以排除仇家滋事的可能。然而這登徒子更不可能是平凡老百姓,難道……是官府中人?
但官府為什麼會動鏢行的東西,還單槍匹馬假冒山賊?這趟押運的物品雖然貴重,卻也不是什麼價值連城的稀世珍寶,如何會驚動官府中人?
金令月陷入沉思,覺得自己像是掉進一張隱形的網,前方有著看不見的巨大危險正等著她……
☆☆☆ ☆☆☆ ☆☆☆
一牆之外。
男子靜靜坐在窗前。
窗外夜色已深,雨早已變小了,淅淅瀝瀝的落在屋簷。
擺弄著手中之物,戲謔之色早已收起,燭光映照下的臉龐清朗剛毅,銳利的眼神帶著絲絲不解。
他細細打量著手中這個扁平的紫檀木盒:盒子是用整塊紫檀雕出來的,盒面雕刻的是「麻姑獻壽圖」。雖刀工精巧,卻並無新意。封口的火漆加蓋了私人印鑑,他打開之前早已確認並未動過手腳。
盒內上下鋪了厚厚一層紅色絲絨,一串指肚大小的合浦珍珠映著燭火,閃耀著溫潤的珠光。
一百零八粒珍珠大小如一,色澤圓潤,配著上好祖母綠雕出的佛頭,光拿在手上,就能教人寧神安詳。
顯然這是一份價值不菲的壽禮,可並不是他想要的東西!
盒底的絲絨早已反覆翻查,並無蹊蹺,盒子也無夾層機關。
祕密到底藏在什麼地方?難道消息有誤?
轉身站起,他低頭對隱藏在暗處的一抹黑影沉聲吩咐:「那邊加派人手盯緊,別出意外。我明天起程趕到漠城,看看他們到底玩的是什麼花樣。你安排人接應。」
「是!主人!」那抹淡淡的人影漸漸沉入更深的夜色中。
☆☆☆ ☆☆☆ ☆☆☆
初隨林靄動,稍共夜涼分。
窗迥侵燈冷,庭虛近水聞。
天色漸漸放亮,下過雨的林間浮著淡淡的霧氣,微風中夾雜著林葉泥土的清香。
幽靜的山中,一座小小的木屋外,兩個身影佇立,遠看,就似畫中的神仙眷侶般美好……
遠看?
對,只是遠看!
「令月小娘子,昨晚沒有為夫在妳身邊,睡得可好?」男子低頭笑看著眼前的麗人,如絲絹的黑髮下是一張俊美無儔的面龐。
金令月雖然仍是一身男兒打扮,眉目間的清爽秀麗卻掩蓋不了。即使這樣身處險境,她依舊沒有忘記將自己保持整潔。
「叫得那麼親暱做什麼,我們之間並未熟識到這種程度吧?」金令月沒好氣的睨了他一眼。
他看得出來她很能忍,然而他卻突然很想看看她眼底的火焰燃燒到最熾烈時,會是怎樣一番光彩奪目。
「為何不能?妳是我娘子。」男子問得很刻意。
金令月一聽見他的話,憤怒的火焰立刻在她眸中熊熊燃燒。
「不許你再叫我小娘子!」她睨他一眼。
她才不要做他娘子呢!
「唉,看來小娘子還不了解為夫。」男子又是嘆氣又是搖頭。「為夫想要的東西從來沒有得不到的,為夫看上了妳,就算妳死了,妳的魂魄也要留在為夫身邊呀!」
男子的神情變得興味盎然,唇邊的笑意有一絲邪魅,浪蕩的輕笑鑽入金令月耳裡,他像一個手段高明的狩獵著,等待著獵物選擇死亡方式。
金令月蹙眉,對他這種霸道的態度相當不悅。
「小娘子別生氣。也許妳還不知道,妳那咬牙切齒的模樣有著無比率真的風情,為夫素來喜歡見到獵物驚慌失措。」
金令月咬緊牙關,握緊雙拳,忍住想將他碎屍萬段的衝動。
女子報仇十年不晚,更何況她現在沒本事和他一決高下,她還要憑著這內力全失的身子拿回被他偷走的鏢物。
「還是……叫妳小月兒好一點?」男子有心激怒她。
金令月強迫自己沉斂心神,向來遇強越強的她,似笑非笑的回以戲謔的話語,「託您的福,昨晚我休息得很好,沒有蠢到妄想憑藉這內力盡失的身子躲過您的覺察,逃出這方圓十里內皆杳無人煙的深山老林。」
「哦?」男子抬了抬俊眉,倜儻的俊臉上盡是興味,「原來妳已經打定主意做我的娘子,跟我一同回山了呀。娘子的款款情意,讓我現在就想吃了妳……」甚是喜歡掌握人心的他存心激怒她。
「你!」金令月強壓下再次高漲的怒火,深知對方不擇手段的激怒她定是另有目的。
她再次自若的對上男子那雙彷似深邃夜空的眼瞳。
「你若是對我心存不軌,大可不必等到現在,所以你也不必用言語激怒我。現下的情形,你似乎不打算放我走,而我的東西在你身上,我是不能、也不可以走。所以,不如你言明目的地是何處,我們也好暫時合作一下,如何?」
「容我自報家門,在下本名秦皓軒,妳可以叫我皓軒。」秦皓軒心中暗暗讚嘆著這女子的聰慧,輕巧躍上馬背,一把拉她入懷,不由她拒絕,揚起手中馬鞭策馬奔馳。
「走吧,我們目的地是漠城。」就先從這一步開始「合作」吧!
他怎麼知道她要去漠城?她從來沒告訴過他吧!
金令月輕蹙著秀眉,蓄意以審視的目光迎上他高深莫測的眼。
她發現他是騙人的,他根本沒帶人,但是昨晚她明明聽到門外有細微的聲響,那些人躲到哪裡去了?
她實在不明白他葫蘆裡在賣什麼藥,但以現在的情況,除了和他「合作」,她別無選擇!
☆☆☆ ☆☆☆ ☆☆☆
深夜,金令月坐在床榻上閉眼調息了半晌後,終於緩緩張開了眼睛。
她從胸前一處大穴輕輕取下一根細長而柔軟的銀針,而後,她輕撫著左手拇指上的扳指,扳指上雕刻著幾朵盛放的梅花,她隨意扳動其中一朵,並把長針纏繞在扳指內,繞好後再扳動扳指上的梅花,將長針藏妥在扳指裡。
「秦皓軒,你有你的張良計,我有我的過牆梯,最終鹿死誰手還是未知數,我們走著瞧!」金令月唇邊綻出一抹詭譎之笑,杏眼中盡是算計。
素來,她金令月就不是任人擺佈之人,就算此刻時不予她、勢不予她,她也會在逆境中尋找致勝之道,畢竟未來是未知的,凡事總有轉變的機會,她的命運掌握在自己手裡,沒人可以左右她。
雖然她表面上答應跟他合作,暗地裡她就按自己喜歡的方式來行動。
拉好衣衫後,她躺在床榻上思索著連日來的線索。
自從她被秦皓軒連人帶鏢一起劫下後,這三日來,她發現一路上都有人暗中為他們安排住處。就像此刻她身處的這小小木屋,屋內乾淨整潔,像是有人事先打掃過一樣。
他到底是什麼人,為何會有人在暗中安排一切?
她愈想愈覺得他身分不簡單。她發現,他雖然身穿百姓布衣,卻全是新製的──遠行之時誰會專門去做這麼多新衣?
而且那些衣衫的面料皆屬佳品、做工更是精細,可謂是粗而不俗……
除非他是為了掩飾本來的身分而專門訂製的!
想著想著,睡意漸漸襲來。
正當金令月欲進入夢中時,房門被人推開了。
她立即警覺地張開眼,並迅速支起身。
甫進門的秦皓軒將門閤上後就走到床前,自然的舉動就像這是他的房間一樣。
「你進來做什麼?」回過神來的金令月冷睨這位不速之客。
「這還用問,當然是準備休息啊。」秦皓軒答得理所當然。
「你走錯房間了,你的房間在隔壁。」金令月捺著性子,以很輕很柔的語氣提醒他。
「我沒有走錯房間。我和妳一起睡。」秦皓軒別有深意的凝視著她,薄唇輕輕揚勾,漾出一抹撩人心魂的魅笑。
因他曖昧的話,金令月的心漏跳一拍,紅霞頓時佈滿了她的麗顏。
怎麼有人可以將這種話說得如此自然!
「你是說……你跟我睡一個房間……一張床?」金令月認真地求證。
「是呀,我們是夫妻,本來就應該一起睡。」秦皓軒不再和她多說什麼,動作飛快地褪去身上的衣衫。
「現在就我們兩人,我們不必假扮夫妻,請你出去。」金令月一手攫住他除去衣衫的手,一掌朝房門的方向伸出,為他指路,逐客之意甚明。
秦皓軒放聲大笑,那夾帶著詭譎意味的笑聲在夜裡聽來格外響亮。
「我保證只是單純的睡在一起,不會對妳做逾矩之事。」他傾身湊近她,彼此之間近至幾乎與她鼻眼相對。「相信我,我是個不近女色的君子。」
他身上流淌而出的灼熱氣息縈繞在她身畔,彷彿要撩動她那平靜的心湖。
金令月皺眉,雖然他信誓旦旦的說得相當堅定,但他俊逸面龐上的笑意,卻有種讓人猜不透的難以捉摸。
秦皓軒看到她欲退離,於是一手扣住她的後頸,強迫她與他對視。
呼吸開始顫抖的金令月努力斂下心神,拚命告訴自己別在意,眼前這個與她鼻尖相對的只是一幅男子畫像,是假的,不要放在心上。
「我能不能問你兩個問題?」金令月努力保持著麗顏上的笑容不變,扯開緊繃的唇,從牙縫裡擠出一句話來。
「好呀。令月想問什麼?」秦皓軒興致很好地挑高眉。
「閣下姓秦,還是姓展?」金令月不悅地睨著他。
「姓秦。」雖不明白她為何問這個,秦皓軒還是如實回答。
「可是柳下惠姓展,敢問閣下是聖之和者──柳下惠嗎?」金令月綻出涼涼的淺笑,眼中透出譏誚的光彩。
慾求不滿的死禽獸!
唉,話說回來,若是他說話非要湊得這麼近,她擔心自己會再也忍不下去,一時衝動出手攻擊!
可是……還是再忍忍吧。目前的局勢不利於她,與對方起衝突並非明智之舉。
「令月不必處處防備著我,這裡是深山老林,我擔心妳會有危險,所以和妳一起睡是出於想保護妳的心。」秦皓軒信誓旦旦的保證自己是個君子,但他的舉動卻像個登徒子──他以鼻尖廝磨著她的。
金令月微瞇起眸瞳,故意忽視唇上不斷吹拂而來的撩人氣息。
「令月突然發現自己『目光如豆』,實在無法看清皓軒的心有多『真』呀!倘若皓軒不介意,可以去找一顆『狼心』給令月見識一番。」金令月語帶暗貶的回敬道。
她在自我嘲笑的同時,也不忘譏諷他胸膛下那顆心是「禽獸之心」。
「有件事我很好奇。」秦皓軒伸出另一手,以指尖勾起她的下巴。「令月想知道是什麼事嗎?」
「那肯定不是什麼好事,還是麻煩閣下在心裡想想就好,不要告訴我。」金令月愛理不理的答。反正她也不想浪費時間聽。
「不行,這事我一定要告訴令月,因為和令月有關。」秦皓軒忍不住輕笑。「看到妳總是一副冷靜自持的樣子,我在想,有什麼事可以亂了妳這份淡然,亂了妳這份自若?」
餘音迴蕩在空曠的室內,一聲一聲,彷似魔咒充滿魅惑力,瞬間將金令月的心弦撩撥得更加紛亂。
眼前女子的內斂冷靜實在讓秦皓軒難以置信。即使是身處弱勢,面對神祕莫測的他,她那份出眾的淡然與聰穎,讓她仍能灑脫地看待世事,並且運謀在心。
縱然他見慣了各種大場面,也不由得對她升出一抹欣賞之意。
可是,他倒是很有興趣知道,有什麼事可以亂了她的淡然自若。
正當金令月被秦皓軒那侵略的目光看得渾身不自在時,他撫在她頸項後的大掌輕輕一按,一股氣勁直衝入她的體內,她頓時覺得渾身虛軟無力。
「不知道……混蛋……你、你想怎樣……」一陣強烈的暈眩襲來,金令月軟倒在床褥中,虛弱得連說話都覺得相當費力。
「令月聽話一點,不要再掙扎了,妳拚命掙扎的模樣只會讓我控制不了一個由心中升起的想法……」秦皓軒故意頓了頓,並迅速褪除身上的衣衫,換上休息時穿的單衣和長褲。
金令月皺眉,怒目直睨著他似笑非笑的俊顏。
「好香……」秦皓軒湊近她,一臉著迷的汲取著她身上沁人心脾的幽香。「令月身上的體香相當淡雅、清新,我十分喜歡,讓我忍不住想日日夜夜抱著妳。」
無力動彈的金令月見他躺至自己身邊,那張惱人的俊顏揚著讓人發狂的邪笑,她忍不住爆出一串「問候」。
「混蛋!禽獸!無恥!卑鄙!下流……」她那顆總是淡然自持的心,被他這突如其來的舉動微微擾亂了。
「令月若是再『送』我一個『問候』的字詞,我就當是某種暗示的邀請!」秦皓軒拉起她的雙臂環上自己的頸項,曖昧的笑聲撩拂在她耳畔,「別擺這種臉色給我看,給我一個笑容。我最喜歡看到令月的笑顏了。」
「可是……」金令月故意頓了頓,拉長了話音,「我個人覺得,看到慾求不滿的淫魔時一定要好好『問候』一番,而我也很樂意遵從我的想法。」她杏眸升起兩簇火焰,目光凜然地直視著他。
此時她最想做的,是好好踐踏他的自尊!
「是這樣的,若是令月不屈服於我的話,我心裡會油然而生一個想法……」秦皓軒一手移至她雪白的玉顏上,長指溫柔地輕畫著。「令月想知道我這個想法是什麼嗎?」
「非常不想。」對於他親暱的愛撫,金令月面龐上一片冰色。
「我這人生來有個獨特的喜好,若是令月對我的想法不好奇的話,只會更加撩動我的心,令月還是別這麼惹我心癢呀!」面對情緒失控的她,秦皓軒柔軟的話語裡帶著威脅。
金令月睜大杏眸,怒焰直襲他似笑非笑的眸子,最終在情勢逼迫下,她不得不妥協。
「不知閣下心裡『驚』人的想法是什麼?」金令月黛眉倒豎。
「令月,有沒有人告訴妳,請教人要謙虛一點,聲音最好是能夠嬌媚到令人骨頭都酥軟了。」秦皓軒要求道。
「盼望閣下『驚』人的想法能給我帶來『驚喜』。」金令月努力擠出嬌媚的聲音。
怕就怕是有驚無喜。
「那就是──倘若令月再掙扎,我會立即撕碎妳這身睡袍,讓妳在名與實上都成為我的妻子。」秦皓軒以蘊含柔情的語氣說道,輕吐而出的字句卻令人心驚膽戰。
金令月隨即挑高了黛眉,以危險的目光橫睨著他。
「雖然我向來不喜歡對手無還擊之力的弱女子下手,但是我相信就算令月此刻無力反抗,妳這玲瓏的嬌軀也能給我帶來不少樂趣。」秦皓軒大掌曖昧地梳撫著她柔順的烏髮。
金令月不語,杏眸卻危險的半瞇,噬人的目光化為銳箭,彷似要讓他嘗嘗萬箭穿心的滋味。
眼前之人的邪惡簡直讓她難以置信。她是不是命中帶衰?還是出門前沒有去祖先靈位前上上香?否則,為什麼她會不小心招惹到這個身分神祕的淫魔?
偏偏這淫魔的能力深不可測,最倒楣的還是她中了對方的暗算,此刻的她已內力全失,被人便宜佔盡、豆腐吃盡,她卻無力還擊!
「令月聽話,別再掙扎,也不要再這樣撩動我的心了。」秦皓軒說得很刻意,「乖乖的做個選擇吧,令月是跟我一起睡,還是繼續掙扎?」他大掌在她背上輕輕的拍撫了兩下。
這威脅般的觸碰讓金令月倒抽一口涼氣,全身繃緊,寒毛豎起。
「令月可要好好考慮清楚呀!雖然妳算不上傾國傾城,但妳絕美的面龐也算是世間少有,妳這玲瓏細緻的身軀更讓人想好好的品嘗一番。」秦皓軒唇角勾揚,扯出一抹壞壞的笑。
金令月凜然直視著他,眸光炯亮如烈焰,彷似要將他焚成灰燼。
秦皓軒再次暗暗運起內力,一股氣勁霎時灌入她體內。
金令月蹙眉,忍住體內翻湧的氣勁,唇角淌下一條細細的血絲。
「令月以為無聲的沉默就是最好的反抗嗎?那妳就錯了,這只會讓我更想明知不可為而為之。」
秦皓軒侵略的大掌懸在她身上,凌空游移,像是正在隔著薄薄的單衣愛撫著她的嬌軀。
他的大掌雖沒有直接碰觸到她的身子,卻也足夠讓她緊張起來,並且豎起全身的防備。
「其實妳這副身軀還真是不賴,曲線亦相當優美,我相信在妳身上,我能找到不少『樂趣』!」秦皓軒以著迷的口吻輕喃,像是在享受著肌膚相親的廝磨感。
經這股強大的力勁一衝,金令月連開口說話的力氣都沒有,唯有杏眸中炯燦的焰芒看得出她的怒意。
「怕嗎?」秦皓軒優美的唇扯開高深莫測的笑,無瑕的俊顏也湊近她,性感的唇懸在她唇上,吹出溫熱的氣息,撩拂著她的唇瓣,似一種勾動人心的挑逗。
「妳流血了,我替妳擦乾淨。」秦皓軒從枕邊拿來她的絲帕,動作輕柔地擦拭著她唇邊淌下的一絲鮮血,像是戀人般溫柔至極。
「混蛋……不要再無禮輕薄,那只會讓我想殺了你……」金令月的聲音很虛弱,但任誰都聽得出她口吻蘊含風暴。
她的話在秦皓軒聽來像是挑釁,而他亦相當樂意接下這飛來的挑釁。
他沉默地結束了擦拭她唇邊鮮血的工作後,將手中的絲帕扔下床。
而後,他優閒緩慢地移動大掌,直至長指輕觸到她微敞的領口,隨即,他以兩指微微挑了挑,之後就沒有再進一步的動作。
這突如其來的舉動怔住了金令月,她的心房忽地激烈跳動起來,未來得及有任何反應,只有一臉錯愕。
「光看令月的粉頸,我就知道,果然如我所想的,令月的肌膚如雪似玉般晶瑩溫潤,真美!」秦皓軒笑得像個色心大起的登徒子。「妳真是秀色可餐,讓我飢餓難耐……」他的眼掃過她領口雪色的纖頸,目光彷似能夠穿透一切般。
「你想怎樣?」金令月的心跳驀然加速,全身戒備。
「令月,信不信我現在就能品嘗妳身上的每一寸肌膚?」秦皓軒輕抿的薄唇彎出一抹戲謔之笑。
金令月緊咬著牙,強壓下被他所亂的心緒,在腦中迅速思忖著應對之計,水眸迸射出高熾的怒焰。
「妳這雙盛滿了狂野怒芒的眸子,看得出來妳的倔強與傲然,這樣的妳太撩動我的心了。」秦皓軒以鼻尖摩挲著她的。「令月聽話,讓我看看妳這張麗顏染上意亂情迷時,是怎樣的誘人。」
金令月不語,沉默是對他最好的抗拒。
見此,秦皓軒停下了折磨她的動作。
「令月認為不理我,我就會對妳失去興趣了嗎?」秦皓軒口吻玩味地反問。
金令月已經是怒火中燒,奈何連續被他兩次以內力「關懷」,此時的她不僅毫無反抗之力,就連說話也相當吃力。
「皓軒……想必你已經玩遍各式各樣的美人身體,令月這種毫無反抗之力的身軀是不會給你任何反應的,當然也無法給你帶來樂趣……你真要動尊口品嘗之前,還請三思呀。」金令月狀似無奈的一嘆。
她扯開僵硬的唇,努力揚起一抹淡然的微笑,想以此告訴他,她沒有把他的舉動放在心上,話聲卻顯得相當無力。
若不是她武功底子不差,方才可不只吐那麼一點血。
「這是令月屈服於我?還是……」頓了頓,秦皓軒挑高一雙劍眉,倜儻的俊顏上盡是興味,「還是聰明的妳在對我下戰書?妳認為妳會有勝算嗎?」
輕觸著她領口的長指緩緩移開,秦皓軒挑起她一束烏絲,纏在指間把玩著。
「皓軒,麻煩你再忍……半個時辰。」金令月忽道。
「半個時辰?」秦皓軒一怔,把玩著她烏絲的指掌也停下動作。
「離這裡最近的洛城,是西邊最出名的刺繡名城,從這裡去到洛城,只需要半個時辰。」金令月泰然答來。
「去洛城做什麼?」秦皓軒很是不解。
「洛城有戶姓蘇的人家擁有最大最老字號的綢緞莊,聽說蘇老爺的女兒更是生得傾城傾國、身嬌肉貴,皓軒可以去佔有蘇姑娘的身子,她會帶給你更多樂趣。」金令月挑高柳眉,扯著唇角漾出譏笑。
她補充道:「以蘇姑娘的嬌弱,無論你怎麼對她,她也不會反抗的。」
「我對那些像死魚一樣的弱者沒興趣。」秦皓軒緩緩而笑,沉沉的笑聲像是摧毀她心防的魔音,「還是會反抗、會掙扎的令月更能撩動我的心。」
金令月才想開口,秦皓軒的長指在她玉顏上輕畫了兩下,隨即才移到她的唇上。
「聽話一點,乖乖的,說妳願意讓我佔有妳,好不好?」他輕輕點觸著她的柔唇,以一種慵懶的誘惑,每說一字,他的指尖就觸碰她的唇一下。
他指尖上的溫度灼熱得像是火焰般,深深的烙入她的肌膚內。
「還請閣下……只用尊眼欣賞一番就好,千萬不要再動尊手撫摸,也不要動尊口品嘗……」金令月扯開緊繃的唇,鎖睨著他的眼神卻充滿了鄙夷。
願意讓你佔有?白癡才會說這種話!
她不停地在心裡提醒自己:此刻不是反擊的好時機,她只能強忍住心中滔天的怒焰,日後有得是機會報仇。
「那就要看令月怎麼選擇了。」秦皓軒似笑非笑的開口,「令月是選擇相信我是個君子、跟我一起睡,還是選擇繼續掙扎?令月的掙扎只會撩動我的心,讓我控制不住自己。」
他話說得那麼輕鬆自然,大掌卻懸在她一方豐盈的雪峰上,雖沒有實際觸碰到她,卻是威脅性十足的動了動指掌。
他在暗示她,將會對她做什麼事,以挑起她內心深處陣陣狂亂的感覺。
無形之中,金令月感覺到一股駭人的壓迫感襲來,折磨著她的心。
「你……我……」金令月扯開顫抖的唇,不馴的怒意佈滿面龐,杏眸閃耀著炯炯的眸光。
「喚我的名字。記得,令月的聲音要嬌媚一點,最好是讓人一聽就想沉醉在妳的聲音裡。」秦皓軒以極輕、極柔的聲音道,卻有一股不容拒絕的威嚴。
「秦皓軒……」
「唉,連名帶姓的稱呼只會更加撩動我的心,讓我想改變與令月的關係。」秦皓軒將唇湊近她,離她的唇只有寸許的距離,並沒有觸碰到她。
他拋給她一記挑逗的飛吻。
「皓軒!」金令月幾乎是吼出來的。
怎麼辦,素來最了解「忍」這一字的她,有生以來第一次有想殺人的衝動,而且是在情勢不利於自己的情況下!
雖然深知此舉相當不理智,但是她真的很想將他碎屍萬段!
「說吧,讓我聽聽令月的答案。」秦皓軒一臉謹慎,像是在聆聽她臨終的遺言,「令月選擇前者,還是後者?」
遇強則強的金令月拚命提醒自己──就算殺意在體內嘶喊,也不能輕舉妄動。目前情勢不利於她,她必須忍住,就算忍出內傷也要忍住,否則一個貿然出手壞了大事,局勢可就難以挽回了。
她那僵硬的笑容,以及眼中高熾的怒焰,都可以看出她忍得很辛苦。
「令月選擇前者。希望閣下不要讓令月失望呀……我這內力全失、又動彈不得的『孱弱』身子可經不起閣下的蹂躪……」金令月唇角勾揚,扯開僵硬的唇,半認真半戲謔地笑道。
「令月是孱弱的女子?」秦皓軒挑高了一雙劍眉,一臉興味盎然。
「對呀,比孱弱女子更孱弱。」金令月從容的開口,「令月可不希望閣下學那些慾求不滿的禽獸,對一個手無還擊之力的柔弱女子出手。」
雖然話是這麼說,但是越看眼前之人,她越覺得他就像個慾求不滿的禽獸……
嗯哼,她突然發現自己忽略了一個驚天「祕密」──他本來就姓「秦」,和「禽獸」五百年前是同一家的人。
「休息吧。」秦皓軒得意地收回手,並以長指在她唇上輕點兩下。
這突如其來的舉動讓金令月怔住了。
他……不會又想對她怎樣吧?
秦皓軒扯來床榻一隅的薄毯,蓋在彼此身上。
接著,他忽地收攏手臂,將金令月緊緊按在懷中,讓她只著單衣的嬌軀緊貼著自己同樣只著單衣的身軀。
怔了怔,金令月眨了眨水眸,未有任何反應。
她錯愕得說不出話來。
他又想怎樣?
「你……」金令月動了動緊繃的唇。
「我們這樣『親密相對』才可以更好的培養感情,扮起夫妻來才不會被人識穿。今後,我們每晚都要這樣『親密相對』。」秦皓軒柔柔的輕笑聲竄進她耳裡,似要摧毀她的心理防線,撩撥起她更高熾的怒焰。
任誰也想像不到,秦皓軒表面上看來像個溫文爾雅的貴族公子,然而在他瀟灑俊朗的外表下,卻隱藏著讓人發狂的邪魅本性。
金令月橫睨著他,一副槓上的樣子。
她擔心秦皓軒會在她入睡時趁機輕薄,因而苦撐著,就算睡意再濃,她也強迫自己保持清醒,以免他對她做出任何逾矩的事。
看著眼前這張無瑕的俊顏,閉目入睡的他,像正處於深沉的思緒中,完全不像方才的輕佻,反而有種內斂的沉靜與溫雅。
若不是眼前之人一直在她身邊,金令月幾乎要以為自己看到了一對容貌相同,但性格截然不同的雙生子。
☆☆☆ ☆☆☆ ☆☆☆
清晨之時,秦皓軒緩緩睜開了眼。
一夜未眠的金令月望著方醒的他,從他那雙半斂半睜的眼眸裡,看到了一種深沉莫測的神韻,更甚者,他眉宇間英氣逼人,無形之間帶著一種震撼人心的銳利。
尊貴的氣質,難捉的神韻,悠淡的神態……
金令月只覺得他是那麼高深莫測,單是憑這股不凡的氣勢,她就知道他並非一般的毛賊。
秦皓軒對上她審視的目光,什麼也沒有說,只是唇邊漾出一抹別有深意的笑,將所有的疑團留在她心中。
江山即將易主,她意外捲入其中──
她不是任人擺佈的棋子,是能與他對弈的棋手!
宇玄《鼎興王朝之逆王狂妃》/11月21日、28日/帝業棋局,執子之手同命一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