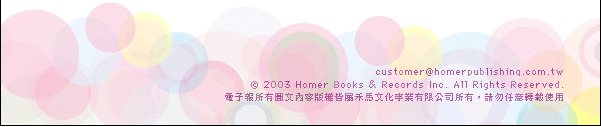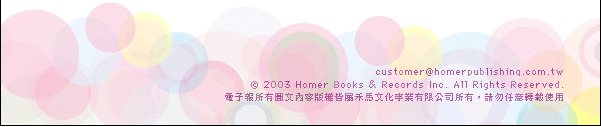|
連載專區:
萬九兒《美人搏命1:二王寵》
☆☆☆ ☆☆☆ ☆☆☆
高校晚自習時間
一個瘦小女生正奮力地爬上花壇──準確說是一座半人高的大花池。
池裡幾座假山高低錯落,水面上浮著小荷葉,晚風吹過波光粼粼。
女生小心翼翼地挪著步子朝花池裡張望,忽然腳下一滑,一百八十度急轉,她雙手亂划,伴著一聲淒厲的尖叫──
「啊……」
叫聲穿透夜空,迴蕩在校園裡,驚起鳥兒雙雙。
女生仰面跌進花池,後腦重重地磕在假山上……
次日,某大二女生不慎跌落蓮花池,傷重不治的消息在校園裡流傳開來。
作為罪魁禍首的花壇,被一圈爍亮的鋁合金護欄圍住。
旁立大告示牌一張,白底紅字寫道──
此地嚴禁攀爬!違者記大過一支,勞動服務一個月!
諸如此類,都是後話……
☆☆☆ ☆☆☆ ☆☆☆
宣元九年,岷山塌陷,天有異象。
大晟皇宮內,鏡湖臨煙閣上,兩道頎長的身影一前一後迎風而立。
「樂卿為何時至今日才回京城?」元帝鳳目低垂,盯著湖面。
「臣在小江鎮誤中青冥散,耽擱了些時間。請皇上責罰!」高大的身影單膝跪地,看起來依舊魁偉挺拔,正是大晟朝忠義侯衛將軍──樂熠。
「起來說吧。事情查得怎麼樣?」元帝沒有回頭,蒼白的病容,臉上平靜無波。
「佛蓮之事,確實讓舜陽王有所察覺,但是,查探的人都被臣誘引至小江鎮以南。日前,臣已將參與人等盡數處理,舜陽王不會得到任何有價值的線索。」樂熠眼芒堅定,穩聲答道。
「朕問的並不是這個。」元帝抬眼遠眺湖面,湖風鼓起他寬闊的廣袖,玉冠下烏黑的髮絲拂過涼薄的唇,單薄的身姿竟似要隨風而去。
「岷山地宮……真的塌陷了嗎?」元帝聲音低沉。
「皇上不是命太常公前去查看?」樂熠抬起頭來,有些意外。
「你當知朕有些話不便問他!」元帝龍顏不悅,驀然回身。
樂熠頓悟,垂眉道:「玉容華的遺骸怕是已深埋在廢墟之下了……」
元帝蠟白的手扶住石欄上的獸頭,骨節被湖風吹得發青,嘴裡絮絮低喃。
「姌兒自入宮就不曾有過一日歡欣,如今又橫死在外,也難怪……她會數度回宮探朕。」
「回宮?!」樂熠著實驚愕,皇上言下之意是玉容華魂魄難安嗎?
「皇上若當真惦念玉容華,可明令太常公在岷山行十日祭禱,臣則前往地宮所在,慰告玉容華在天之靈。」看元帝神情愴然,樂熠開解道。
元帝沉吟片刻:「這……不會令舜純起疑嗎?」
「應當不會。」樂熠搖搖頭。「玉容華為助皇上尋找佛蓮,在宮外的彌陀庵假借避疾隱居半年,麗嬪娘娘再有心也難將皇上的計畫和玉容華聯繫起來報知舜陽王。
「至於近來舜陽王有所警覺,依微臣看,皆因得知皇上之前曾漏夜出宮。至於皇上究竟所圖何事,他並不知曉,不然,他也不會在小江鎮查探無果後,夜半時分讓一隊重騎,明火執仗,沿岷山山道返回晟京。其意顯然是在敲山震虎,讓皇上有所避忌,以此來阻撓皇上行事,實則計窮。
「況且在世人看來,山體崩塌乃是天象,與人事無干。微臣此去祭悼,謹慎行事即可,舜陽王與麗嬪未必猜得透其中關竅。」
「那便如卿所奏。」元帝聽罷,面色稍霽,思忖片刻後又冷笑道:「敲山震虎之計?單憑舜純,他能有震懾朕的氣魄?哼,那一隊重騎是朕的皇姊在敲打朕!」
樂熠微微頷首,深以為然。
☆☆☆ ☆☆☆ ☆☆☆
結束了岷山的十日祭祀,樂熠回到西街的忠義侯府,密室內一墨衣人等候已久。
「跟丟了?」樂熠目光灼灼,面露薄怒。
地上跪叩的人深深地俯首下去:「請主子責罰。」
「可是有人接應她?」樂熠沉聲問道。
「沒有。是……是梟羽大意所致。」地上的人艱難的說道。
樂熠怒極反笑,威嚴的唇邊閃過一絲戲謔。
「你的意思是說,梟羽怠忽職守,跟丟了人?陸平海,你身為一堂之主,大意所致這話是從你嘴裡吐出來的嗎?!」
陸平海暗自頭痛,梟羽跟在侯爺身邊多年,年紀雖輕,歷練卻不少。這次竟將一個羸弱少女跟丟,豈不可笑?
任務是侯爺直接交給梟羽的,出了這等事,梟羽自知一紙鴿信交代不了,卻又不敢擅自離開建州。事情出在他陸平海的地界上,也只得他這個飛鷹堂堂主回京給侯爺面稟。
陸平海思忖再三,還是將梟羽的話原樣兒道出。
「梟羽回報說,主子要他一路暗中跟著保護的那位姑娘,每日都只是趕路,日行不過三、四十里。後因風餐露宿,患上風寒,住在建州境北吳家鎮上的客棧,期間一直發熱不止,昏睡在床,梟羽潛進去看過脈象,並無大礙,只需在客棧裡好生服藥,安養一段時日,即可痊癒。
「哪知一日清晨,梟羽再去看時就發現……姑娘已經不見了。小二與掌櫃都講不清去向,只說天沒亮姑娘就結帳離開了。梟羽再出去找,就已斷了線索。」
樂熠聽得認真,直到陸平海說完,才又問:「她一路上諸事可都尋常?」
陸平海斬釘截鐵道:「是。梟羽也是有些歷練的,若有異常,必瞞不過他的眼睛。」
樂熠冷笑道:「瞞不過他的眼睛卻能把人弄丟?這帳,本侯日後再與你們算!」
樂熠心中已明瞭她為何天未亮突然離開,是銀子!他常年在外征戰,少年時有過一段艱辛的日子,自然知道出門在外,生病住店,要花去多少金錢。
當初他為了掩飾身分,僅以師徒之名相助,離開時只給她留下些碎銀,匆匆之間也不曾細想,一個小姑娘南去閔州千里迢迢,難免身子撐不住會生病。
她必然是發現銀子不夠使,才一早結了房錢悄悄離去。偏生梟羽也不知道會有這一層緣由,一時大意,便跟丟了。
只是如今她有病在身,又沒了銀子,能去哪裡?連梟羽都找不到,難道又去做了乞丐不成?
陸平海見樂侯面色晦暗不定,魁偉的身子不斷在室內來回走動,綸巾青衫颯颯有聲,不禁心中忐忑,埋怨梟羽害他不淺。
片刻後,樂熠頓住身形,沉聲道:「讓梟羽繼續在虞山吳家鎮一帶尋找,若是一月後還不見人,就在前往閔州的途中一路安排人手。她必是要從建州南下返鄉的,讓梟羽沿途截住她,帶回晟京。」
話雖如是說,樂熠卻心中悵惘。若是她不返鄉,臨時換了去處,自己又待如何,又能如何?
一念及此,樂熠竟有些暗悔自己不該授她易容之術,更不該讓她一個荏弱女子孤身上路,現在想要尋找,著實麻煩。
心中悶煩,樂熠又衝著陸平海喝道:「還不速去!告訴梟羽,若是找不到人,他也不必再回來了!」
陸平海哪裡還敢再言,忙出了密室,連夜快馬加鞭,趕赴建州。
☆☆☆ ☆☆☆ ☆☆☆
建州境北,虞山靜慈庵。
佛堂裡檀香氤氳,供案上的長明燈搖曳著暖暖的昏黃。
初苒仍在沉沉的夢魘中掙扎,夢裡帷幔如雲,紅燭如晝。
正在床笫征伐的帝王身姿修長,肩背清瘦而寬闊,床榻上的美人釵橫髻亂,醉眼微殤,一雙玉臂春溶水漾地纏附在帝王的頸項上……
「皇上,啊……皇上……」
夢中的美人驚呼著弓起,嬌喘連連,如玉的肌膚上綴滿晶瑩的細汗,身子在燭光下顫抖得似疾風中的弱柳,又如岸邊被反覆推送揉搓的浪花。
俊美無儔的帝王下頷高高昂起,髮絲黏在頎長的頸間,眼簾緊闔,薄唇微啟,滾動地喉中發出動情的低吟。
初苒額上沁出密密的細汗,嘴裡不斷嘟囔著,想走卻怎麼也走不脫。
「呼──」
一聲長息,初苒終於掙扎著醒來。
手背拭過額上的細汗,強撐著取過小几上簡陋的銅鏡,看著鏡中模糊的容顏,初苒再次嘆了口氣。
這張臉不是自己熟悉了十九年的臉,這身體也不是自己的身體。說到底,還是自己貪生……
初苒覺得人真是世上最奇怪的東西。
在二十一世紀,日子自由、舒適,但她覺得無聊死了。魂穿來到異世的這數月,生活備嘗艱辛,還頂著別人的容顏,她卻一心想好好活下去……
窗外的黑幕漸漸退卻,天色已然泛白。
靜慈庵的殿門「吱呀」一聲被推開,涼風裹挾著初秋的寒意,竄入帷幔後的內堂。
初苒纖巧的手掩住蒼白的唇,卻忍不住急促的輕咳著。
一個圓臉的小尼姑快步走入內堂,將手中厚實的僧衣披在寒症未愈的初苒身上。
「于施主,今日可有好些?」
初苒笑著點頭,怕她不安心,又拍拍她攙在自己臂彎的手。
這圓臉的小尼姑法號「圓了」,給圓了起法號的住持師太,也算得上是佛門界的一株奇葩。
小尼姑就著窗外的晨光仔細端詳初苒的臉色,一雙圓眼瞪得黑白分明,裡頭盡是擔心。
初苒又笑了。從前她絕不稀罕這樣廉價的憐憫,但是現在她卻懂得珍惜萍水相逢的點滴友情。
幾聲木鈴「篤篤」,該是眾尼上早課的時間了,初苒忙伸手指指門外,圓了這才一步一回頭出了大殿。
裹緊圓了送來的僧袍,初苒走下禪榻,寒氣順著腳心一路上來,激得她滿眼色彩斑斕。
扶住額頭,緩步挪出內堂,初苒在大殿的蒲團上跪下,雙手合十虔心祝念。
杏黃的幔帳下,一尊通體鎏金的菩薩,寶冠瓔珞,面龐甚美,卻不知名號。
圓了稱之為菩薩娘娘,還說初苒是菩薩娘娘轉世。其實細看容貌,她與菩薩娘娘並不相似,大約在圓了單純的眼裡,太美麗的事物總是相像的。
以初苒的直覺,這靜慈庵還有庵裡的眾人都和這尊菩薩娘娘一樣,有些說不出的不同尋常。但她只是個過客、寄居之人,又怎好無端揣測妄議,不過一笑作罷。
祝禱完畢,初苒剛踏出殿門,就見圓了端著一只粗瓷碗滿臉笑意地走來。
碗裡是用各色豆子、乾果熬的米粥,居然還放了油鹽佐味。初苒看得眼眶一熱,這裡是尼庵,圓了花了多少心思才熬了這粥可想而知。
幾日前,初苒暈倒在庵門口,也是圓了救她進來。
靜慈庵的規矩是不留宿香客,虧得圓了一直說初苒是菩薩娘娘轉世,儀修師太才發了慈悲把她安置在慈安堂暫住。
按輩分,這位儀修師太是庵裡的師伯。三、四十歲年紀,容顏俏麗靈動,眉眼跳脫,沒有半分出家人的清寂。但住持師太很尊重她的意思,初苒得了她的允准,住持師太也就沒再說什麼。
白日裡,圓了洗濯僧衣、打掃大殿,初苒便在一旁幫她晾曬、擦拭。累了,就坐在慈安堂的門檻上,笑著看圓了忙進忙出。
晚上,儀修師太帶著圓了來慈安堂誦經,初苒便虔誠的跪坐一邊旁聽。
身體一日好過一日,初苒心懷感激。老天也算待她不薄,總在她以為要山窮水盡的時候,又給予她堅持下去的力量。
好比圓了,好比之前窮困潦倒時願意傾囊相授的師父……
☆☆☆ ☆☆☆ ☆☆☆
這晚,聽完住持誦經,初苒便早早睡下,朦朧中似乎聽到佛堂裡有人說話,仔細分辨原來是住持師太的聲音,好像還有儀修師伯。
「師太,可是有什麼事?」初苒忙披衣起身,出來問道。
聽到初苒驟然出聲,說話的三人都轉過頭來,初苒也吃了一驚。
此時殿內除了住持和儀修,竟然還站著一個二十來歲的年輕公子。玉色長衫,錦帶束髮,丰姿俊逸,只看他安靜地站在燈影裡,便讓人覺如竹風入林,琴瑟齊御。
初苒有些無措,見自己衣衫還算整齊,住持和儀修師伯又都面色坦蕩,且與那年輕公子極熟稔的模樣,才穩住心神向住持說:「師太,我出去倒些茶來。」
端了茶,初苒遠遠站在廊下背風處,並不進去。
庵裡的眾尼都已經歇了,一輪秋月高照在堂前香爐上。
初苒靜靜地呆看,心中俱是驚疑和不安──那位年輕公子的容貌,竟與自己魂遊大晟宮時看到的元帝有六、七分相像。只是元帝消瘦病弱、額青頰凹,多隱忍靜默,沒有這位公子的恣意灑脫、丰神雋秀。
過得一會兒,年輕的公子施施然出來,住持和儀修師太謙恭的跟在後面。
繞過前殿時,儀修師太忽然停下,揚聲道:「蕭施主請留步。蕭施主這次來做法事,是為了行善積福,不知可願再行一善?」
那公子回過身來,清俊的眼中閃過一絲莫名。
儀修師太指著廊下的初苒:「蕭施主素來知曉,庵裡是不留宿香客的。但這位于施主身世孤淒、心性良善,又有痼疾在身,故住持破例留她在庵中暫歇幾日。然寺規在上,日久終是不便……」
說到此處,儀修師伯聲音漸柔,俏麗的眼中也染上了淺淺的笑意。
「若蕭施主肯帶她到山下別院調養,他日于施主痊癒,蕭施主便是功德一件,貧尼也了了一樁心事,豈非兩全。」
初苒霎時怔住,指甲生生嵌進木製茶盤裡。說不清心裡是悲是怒,抑或寄人籬下多日,自己竟軟弱麻木得說不出一句話來。
那蕭公子瞥初苒一眼,又深深地看回儀修師太,嘴角牽起輕笑。
「無妨。」
住持聽罷,也轉過頭來對初苒道:「于施主,庵中清苦,於妳養病無益,妳只管與這位蕭施主下山去吧。」
不容置疑的語氣,斷了初苒最後一絲指望。
「謝謝師太多日來的照顧,且容我去和圓了道別。」初苒神色淡然。
走進禪房,初苒坐在榻畔輕推圓了,喚了好幾聲,圓了才懵懂地起身揉眼。
初苒不捨地握著圓了的手,「圓了,我要走了,以後也不知道還能不能再見妳,我會常常想妳的。若妳也想我就去和菩薩娘娘說,我一定聽得到。」
說著,初苒眼眶就熱了。見圓了還是一副迷迷糊糊的樣子,只得苦笑著讓她躺下,又替她蓋好被褥才默然離開。
回到內堂換下僧衣,初苒給菩薩娘娘磕過頭,便拿著自己的小包袱出了庵門。
那位蕭公子果然冷著臉等在山門外,身旁還多了一個高大的隨侍。
初苒默默低著頭跟在他們身後,乘著月色一步步下山去。
到了山腳,初苒立在路旁不肯再走。「蕭先生的好意,小女子心領了。其實我的病早已痊癒,只是捨不得圓了小師父,才在庵裡多待了兩日,不想竟給住持師太添了許多麻煩。如此皆是我的不是,現下又怎好再去擾先生清靜?虞山去吳家鎮的路我很熟,先生不必憂心,就此告辭。」
蕭公子轉過身來,看向這個身量尚不及自己肩高、十四五歲的半大小人兒。
迷濛的夜色下,模樣不甚清楚,只有一雙顧盼靈動的烏瞳熠熠生輝。她氣鼓鼓地梗著脖子,小嘴開開合合,硬邦邦地繞出大通的官話。不甚豐盈的胸腔,起起伏伏,想必裡頭衝撞的盡是憤懣與憋屈。
蕭公子無端生出一種惡趣的暢快,以至於樂不可遏的揚聲大笑起來。
初苒一臉錯愕,不知何事引他發笑。這裡雖然算不上荒山野嶺,但是這等笑聲在夜間實在刺耳。
方才在山上時,他還是一副溫恭謙和、君子如玉的模樣,這一刻卻又變得喜怒無常、狂放不羈。
嗒嗒嗒……一陣馬蹄聲打斷了初苒的腹誹。
一個少年駕著馬車悠悠駛來,車後還跟著一匹溜光水滑的駿馬,蕭公子翻身上馬,韁繩一抖揚長而去,滿臉的笑意猶未退卻。
初苒還在好奇的張望,就猛然覺得衣領一緊,身子就離了地。
蕭公子帶來的高大隨侍將她提在手中,向馬車走去。
初苒還想再掙扎,卻發現她已經手腳麻木、口不能言……
山路顛簸。
初苒被扔在車內,側身蜷臥,頭一下一下的在車壁上來回磕碰。
大病未癒,初苒的腦子被搖得如同圓了熬的粥一般,一塌胡塗。心裡更是憤怒,自己與他們前日無怨近日無仇,這是什麼尼庵什麼善人?
三更半夜,把一個病丫頭趕出尼庵,扔給了一個來歷不明的紈袴公子。這就是今後她要面對的世界?何止是不平等、不公道,簡直沒天理!
如此走了半個時辰,馬車才停下來。初苒早已被搖得兩耳嗡嗡,眼前影影綽綽。
朦朧中自己似乎又被提出了馬車,許多燈光,許多人影。
最後到了一處極柔軟溫暖的地方,初苒就眼前一黑,昏死過去……
☆☆☆ ☆☆☆ ☆☆☆
晨間,初陽窺探的光斜斜地穿過鏤花窗櫺,投在牙色的繡帳上。
一隻纖柔粉嫩的手伸出錦被,捏成小拳。淡而修長的眉擰出調皮的弧度,略顯蒼白的唇瓣不耐的噘起。
「呃啊……」
似是極舒服的懶腰,才剛伸到一半,帳中的人就猛的一個激靈坐起,像受驚的鳥兒一般跳下床來。
過了昨晚,初苒真的不曾料到自己還能有這樣的待遇。房中繡榻綿軟,陳設清雅。自己還穿著昨晚的衣服,小包袱也原模原樣兒安放在枕邊。這就是那個什麼蕭公子的別院吧!
初苒無力的在桌前坐下,身心俱疲,實在沒有勇氣再去推那扇掩著的門。
「叩、叩。」房門外傳來幾聲輕叩。
「姑娘可是醒了,可要奴婢們進來伺候?」有侍女低聲謙恭地詢問。
初苒起身,房門被推開一條小縫兒。幾聲輕語過後,兩個穿著麻衫的丫頭垂頭躬身,捧著盥洗之物進來,托到初苒面前。
一個梳著低髻的侍女將一匣衣服放在妝臺上,向初苒道:「秋涼了,姑娘穿得太單薄,莊裡一時沒有合適的衣服,姑娘且先將就些。」
初苒坐在妝鏡前,看著她們給自己梳起低髻,又換上與她們一般無二的麻衫,儼然一副小侍女的模樣,反倒寬心不少。
用過膳食,侍女們自行出去。房門大開,初苒試探著出去,也無人阻撓。
這裡是一處極清幽的山莊,山莊不大,依山而建,有梅蘭松竹菊五個院子,她住的地方叫隱松齋。院裡丫頭僕役各司其職,見了她除了低頭行禮,沒有半句閒話。
融融的秋陽暖如母親的大手,時而柔柔地擱在髮頂,時而暖暖地撫在背上,讓人想不舒心都不行。要說,這般清雅閒適的所在,當真是個養病的好地方。礙眼的,只有那兩扇緊閉的莊門和四下裡高高的山牆。
晚間時分,一個丫頭過來傳話,「主子請姑娘去宜蘭苑用晚膳。」
初苒頓覺寒毛直立,心驚如兔,跟著那丫頭踏進一座大院,還沒進門就聞到燒鮮魚和燜肉的香味,她寡淡已久的胃瞬間叫囂起來。
前廳,偌大的飯桌旁只擺了兩張椅子。
其中一張已被英明神武的蕭大公子坐了,初苒只得坐在另一張椅子上。
丫頭們關上廳門,眼觀鼻鼻觀心的立在兩側,這樣的氣氛,讓初苒登時如坐針氈。
蕭大公子眼皮都沒抬就兀自開始用膳,動作雖斯文有禮,態度卻倨傲得似乎對面無人。
這算是嗟來之食?初苒立時覺得一股怒氣「呼」地自腦門奔竄而出,在髮上盤旋數周後,又遊回七經八脈,獨留一縷清煙自頭頂嫋嫋而上。
她固執的坐在椅子上一動不動,眼睛緊盯著自己膝上平放的雙手,那蕭公子卻如未見一般,獨自吃罷,接過丫頭遞上的茶盞手巾,起身睨了初苒一眼,就隨意歪在一張坐榻上執起書卷遮住臉。
廳內寂靜無聲,只聽得書卷翻過一頁,又一頁,又翻一頁。
丫頭們垂眉斂衽站得筆直,廳門關得死死的。
良久,「吱呀」一聲,侍人們悄聲推門進來,將已冷的飯菜端了下去。少頃又熱騰騰的端上來,依舊關了廳門出去,一句多的話都沒有。
初苒兩手不由得死死的揪住袖口,滿腹怒氣與委屈,肩頸繃得僵直。
一刻鐘後,飯菜又熱了第二趟。
初苒直起痠痛的脖子,再看過去時,發現那位蕭大爺竟然用書冊蓋了臉,支起一腿仰面躺在榻上,睡、著、了!
死死盯著書冊,初苒捏緊拳頭,恨不得立刻起身衝過去揍那書冊下可惡至極的臉。
她是一刻也不想再在這裡待下去,恨恨地抓起筷子扒光飯菜,重重地摔門出去。
「呃啊……」身後傳來蕭大公子愜意的呵欠聲。
初苒掩面狂奔。節操啊,就碎在眾目睽睽之下。
這位大爺前世定是無賴託生,不然怎地會如此面目可憎!
第二日,第三日……
初苒忽然覺得自己大可不必和飯菜較勁,與無賴當真,只需每餐吃上八分飽,而後甩手離開便是。
這天,碗中的飯粒又快要見底時,一只圓胖的掐花蓋碗忽然被推到初苒面前,揭開碗蓋,氤氳的熱氣下是一碗澄明微褐的湯,光聞味道就知道是好東西,初苒眼皮都沒抬,便乖乖地喝了,湯入口微苦又漸漸回甘,裡頭蔘定是少不了的。
無視蕭大公子戲謔的眼神,初苒正預備起身離席,帶著笑意的聲音卻從對面傳來。
「往後,都像今日這般才好。」蕭大公子滿意地說道。
「多謝先生謬讚。」初苒冷笑回應。
「姑娘來了幾日,可還習慣?」蕭公子唇角帶笑,饒有興致的問。
初苒暗自磨牙,面色不耐,心中覺得他甚是犯賤。
「嗯……照今日看來,姑娘必是習慣的。」蕭公子卻似乎渾然不覺,自顧頷首。
初苒怒氣又衝出鼻腔,冷哼一聲,依舊只是垂眉視地。
「在下還不知姑娘芳名……」蕭大公子揚眉一笑,站起身來踱著步子,「不知道也罷。姑娘既是孤女,從前的俗名丟了便是。在下看,姑娘眉目靈動,顧盼生情,就叫盼兒,可好?」
盼兒?初苒一愣,這是要把她留在莊子上做丫頭的意思?
她何時竟成了賣身的奴婢!不自覺間,初苒長睫撲扇,修眉怒挑,一雙煙水明眸直直地瞪了過去。
「哈哈哈……」蕭公子立時拊手失笑,「就是這般!嗯,以後就叫盼兒吧。」
初苒立時無語,轉念卻又想,他不追問她姓名來歷未嘗不是件好事,是以唇帶譏誚地笑問:「盼兒謝先生賜名。只是盼兒受先生之恩多時,還不曾得知先生名諱,實在有些惶然,不知今日可蒙先生賜教?」
蕭公子沉吟片刻才說,「在下蕭鳶。」
初苒心下哂笑,看樣子他也不願吐真名。
「先生名諱果然情志高遠,盼兒日後定當去靜慈庵求取長生牌一面,將先生名諱鐫刻其上,供於盼兒房中,日日高香明燭,為先生祈禱福壽,以謝先生收留之恩。」
笑容僵在臉上,蕭鳶滿眼山雨陰沉,廳中氣氛頓時有些凝滯。
想起昨日,儀修師太派人送來一封書信給他,信裡說什麼皇后娘娘託夢,憐皇兒煩鬱孤寂,故遣一福慧無雙的女子前來陪伴。
根本一派胡言!也不知這個來歷不明的丫頭怎麼入了儀修姑姑的眼,非要塞到他身邊來。他怎麼就沒從這丫頭身上看出半點福慧無雙的樣兒?
哼,還高香明燭將他供在房中拜祭!這是把他當做什麼?本來瞅著這丫頭耿直有趣,身上又有幾分尋常女子難得的風骨,還打算放在身邊留用,但是今天她卻敢當眾消遣他,如此還能指望她來紓解煩鬱?遲早被她白白地氣死了才是真的。
蕭鳶──也就是當朝五皇子蕭子珩──百般氣悶,卻也拿儀修師太無可奈何。
這位儀修師太原名倩儀,是先懿德皇后長春宮裡的司茶女宮,頗得先皇后喜歡。先皇后薨逝後,長春宮裡的宮人大多跟隨先皇后入了孝陵,唯獨倩儀執意留在長春宮,每日打理皇后生前居所。
先皇后是齊姜國人,一生育有二嫡子。太子生於辰時,取名辰昱;五皇子生於子時,取名子珩。
景帝廿七年,蕭子珩被冊封為懿王,賜婚趙氏嫡女靜柔,並著大婚之禮與太子納妃之典同日進行。
一時,盛況空前,舉國同慶。
然而大婚當晚,一紙驅逐詔書卻毫無先兆的發至景福宮中,新婚的懿王蕭子珩被勒令即刻奉旨出京,連夜起程前往封地建州,自此,非詔不得擅離封地半步!
喜慶的燈火映得天幕如彤,宮牆下的暗影裡,淒冷的夜風猶如利刃掠過人們的心房。
十四歲的懿王殿下身著大紅喜袍,在侍衛的脅護下,攜著新婚的懿王妃,徒步從景福宮出來,在朱雀門登上簡陋的車輦,帶著寥寥數十騎,踏上了前往建州的路。
倩儀驚聞懿王被遣出宮,將一頭青絲絞得七零八落,抱著長春宮裡供奉的懿德皇后玉像,闖出宮門,跟隨蕭子珩而去。
一年後,景帝駕崩,太子蕭辰昱即位,史稱元帝。
當年,蕭子衍離宮突然,連已故的先皇后都不及去拜別,更別說知會親信,召集故舊了。因此,現下要說起蕭子衍身邊的親近之人,竟只有這倩儀姑姑一位。
宮中出來的女子不可再入紅塵,入建州境時,蕭子衍命人重修了虞山後的尼庵,將母后的玉像和倩儀姑姑一併安置在庵中,題名靜慈。
先前,圓了口中那尊容顏美麗的菩薩娘娘,正是懿德皇后的造像。
每逢先皇后生辰死忌,蕭子衍都會北上虞山,到庵中拜祭母親。
今年遇到了初苒……
☆☆☆ ☆☆☆ ☆☆☆
初苒托腮坐在桌前,百無聊賴地盯著爐鼎中嫋嫋的息香。
近來,她的脾氣似乎越來越大,每次看到那個魔頭,就會生一肚子閒氣。難道這就是傳說中的庸人自擾?
按理說,那魔頭既沒關著她也沒鎖著她,每日還有藥膳給她養身,雖說是少了些自由,然則,好過是一天,歹過也是一天,身子不好起來什麼都是浮雲不是?
初苒伸手捏捏懷中那只精巧的小皮囊,它可對付不了莊中這麼多一等一的高手侍衛。還是得先穩住了局面,徐徐圖之才好,離開的機會總是有的。
山中無日月,一晃就是數十日。
得罪了蕭鳶的初苒,很快成為山莊中侍女的一員。
藥膳倒是沒有打折扣──也是,像蕭鳶這樣的貴人,怎會稀罕區區幾支蔘。
秋意已經漸濃,庭前的落葉一夜之間就鋪得滿地,初苒卻如春日綻放的桃李一般,日益明媚鮮妍起來。
中秋佳節時,初苒穿著鵝黃色的新裙,仰著粉嫩的小臉兒,俏生生地站在桂樹下摘桂花。長睫映在煙水濛濛深眸中,柔美動人的頷線一路延伸到微敞的交領裡。如瀑的烏髮被綢帶鬆鬆綁住,在纖細窈窕的腰肢後調皮地搖晃。
淘好的桂花最後被送到廚下去做桂花糕,初苒挽起的袖管裡露出一段瑩潤的梨花白,滿身的花香撩撥著人們的口腹之慾。僕役們紛紛低下頭去,耳後一片通紅。
凡此種種,莊裡的蕭大公子自然不會後知後覺。
晚宴過後,皓月如銀。
蕭鳶命人點了數十架燈燭,將初苒那張吹彈可破、燦若丹霞的小臉兒細細地賞鑑一番,立時心情大好,朗聲說道:「果真是養好了,下大賞!」
「謝主子賞賜!」
「主子萬福金安!」
燈影裡立時烏壓壓跪下一片,廳外廊下都洋溢著歡慶。
次日,莊中如節慶沒有過完一般,每個人都笑著忙進忙出。
眾人見了初苒,連「姑娘」都喊得格外大聲!
初苒心下狐疑,這是領了多大的賞,竟有這般高興,何故自己沒有?
直到午後初苒才打聽得明白,原來是混世魔王蕭鳶要回雍都府邸去了!
真是日月齊升、天意見憐!祈禳眾生翹首以盼的都是這一日啊!
山莊只是別院,魔王早晚要回他正經家去的,是自己氣昏了頭竟忘了還有這一層。初苒傻笑著搔搔腦袋,如今她已「一朝病癒」,儀修師太所託的善事,蕭鳶已功德圓滿,說不定這就會放她離開。說到底,她並不是莊子裡賣身的奴婢。
籠罩多日的陰霾統統散去,初苒甚至都想去宜蘭苑感激一番──順便辭行。就算蕭鳶不肯放人,只要他先離了這裡,莊中少了侍衛,她還怕沒機會離開?
初苒心頭想著,腳下就不知怎地踏進了宜蘭苑,等在書齋外求見。
蕭鳶依舊一襲秋衫,錦帶束髮,三分風流七分風雅。見初苒一臉雀躍地進來,便斜簽了身子靠在窄榻上,唇角含笑翹起。
初苒在莊中待了月餘,如今已是粗通禮數,當下疊起小手,深深地福下身子:「盼兒蒙先生照拂多時,今日聽聞先生要回雍都府上去了,只怕日後無緣得見,特來面謝先生收留之恩,一併祝先生路途平順與家人早得團聚。」
聞言,蕭鳶立時斂了笑,眉眼陰沉,端起茶盞,疏離地問:「是誰說,妳要留在莊子裡的?」
初苒聞言驚喜,「是是是,盼兒叨擾先生多日,如今既已痊癒,自然沒有再留下的道理,盼兒這就去收拾行李。先生的大恩,盼兒銘記在心,日後定當高香明燭……」
砰!茶盞重重的落在桌案上。
蕭鳶忿然走下榻來,再回頭時,陰沉的臉卻又笑得和煦,話一字一字從牙間蹦出,「原來盼兒姑娘是來辭行的!不知,姑娘可有去處?」
初苒驚魂甫定,烏瞳顧盼幾下,「眼下暫無去處,不過吳家鎮、虞山這一帶都還算熟悉……」
「那敢問盼兒姑娘,日後有何打算?」蕭鳶的身子漸漸壓下。
初苒貓了貓腰,勉強道:「我……可以去找師父。」
「噢?盼兒姑娘居然還有師父!」蕭鳶笑得愈發妖孽。
初苒頓覺頭皮發麻,口齒僵硬,真話壓在舌下,再不敢吐露半分。兩扇長睫忽閃如翅,不經考慮的瞎話順嘴胡溜,「聽、聽說,東海有座蓬萊島,島上……有位天孫大人,繡藝無雙,織出錦緞可比漫天雲霞。盼、盼兒想去拜師學藝。」
「嗤!」
頭頂傳來一聲大大地哂笑,初苒的腦袋瞬間就耷拉了下去。
俗話怎麼說來著?樂極生悲!
現在極樂的是榻上坐著的那位,悲從中來的是自己!明知道那是個無賴,好死不死的,跑來惹他做什麼……初苒無比怨念。
噠、噠、噠……修長的手指在桌案上輕叩,蕭鳶眼裡沒有半分初苒想像中的喜悅,幽深的眸底盡是陰晦,清俊的臉向著窗外。
少頃,蕭鳶忽然朝門外揚聲問道:「莫青!都準備好了嗎?」
莫青一臉茫然的從門外進來,躬下身子忖度著說道:「大半備得差不多了,要不奴才給主子看看去?」
「不必了。更衣。」蕭鳶站起身來。「讓莫大去準備馬車,半個時辰後起程回雍都。」
初苒和莫青的下巴都同時掉到地上了!
初苒抬起頭來,結結巴巴的指著窗外說道:「先、先生,再一個時辰天就黑了。」
「那又如何?」蕭鳶側目斜睨,似笑非笑。
初苒伸出的手指再次無力了。
蕭鳶經過初苒身邊,俯身說道:「盼兒姑娘的隨身之物不多,自然也無啥好收拾的,就在此候著吧。」
一時間,平日裡大氣兒不見一聲的宜蘭苑,頓時忙得人畜大亂,雞飛狗跳。
初苒獨自站在書齋裡,恨恨地勾回手指,磨牙默道:「我忍!」
半個時辰後。
初苒抓著一只乾癟的小包袱,站在高大的馬車前,內心滿是怨念──所有人都騎著高頭大馬整裝以待,而蕭鳶自然是坐在馬車裡的!她怎麼辦?
要抗議嗎?那是無用的……
莫青伸過胳膊,初苒扶著上了馬車。她正猶豫著要不要賴在車轅上坐下,莫青卻極無辜的站在車下,雙眼頻頻忽閃,似乎在說:姑娘,那是我的位置。
初苒只得悲摧的推開車門,蜷縮著進去。
車外的莫青長長吐了口氣,跳上車轅,手一揚,莫大「啪」的一記鞭響,馬車緩緩動了。
車內,蕭鳶又執起一冊錦卷遮了臉。初苒頓感無力,心內腹誹:要不要這麼幼稚?你就不能換個花樣嗎?
反正自己的臉如今也已百煉成鋼,初苒若無其事的靠著馬車側壁坐下,將手肘擱在身邊的梨木小櫃上,百無聊賴地盤算心事。
忽然一隻手朝她胸前伸來,初苒下意識朝後躲去,頭「咚」的一聲磕在馬車側板上,頓時疼紅了眼睛。
瞪著那隻不知死活的罪魁禍「手」,初苒揉著後腦就打算發作一番,忽然意識到自己身著「丫頭制服」,她又洩了氣。
認命的溫好茶盞,初苒斟上半盞熱茶,遞在那隻執著的手中,又拿銀箸從食盒中揀出幾色吃食,用小碟盛了擱在漆盤裡,放在那人身側。看見他飲了茶,愜意地拈起一塊點心享用,初苒這才輕輕地吐了口氣,坐回角落去。
車隊晃晃悠悠走了一兩個時辰,寒意漸起,琉璃窗格外夜色如墨。蕭鳶也棄了錦卷,側身向裡睡下,漆黑的髮絲鋪散在枕上,身上隨意蓋著一件玉色大氅。
初苒起身將窗格上厚厚的織緞簾子放下,自己也裹了件棉披風,枕了胳膊伏在梨花小櫃上打瞌睡。馬車上的睡姿十分不舒服,初苒最近日日精養,現下竟是半分睡意沒有。俯仰轉側,漸漸搜腸刮肚餓得難受。本來莊子裡是備了飯食的,出發前大家都吃過了,偏她在嘔氣,沒吃兩口,結果現在餓得夠嗆。
聽蕭鳶呼吸綿長,似乎睡得正沉,初苒輕輕挪到矮几前,取出一碟糕點,貓著身子悄悄地吃。果真人餓的時候東西格外好吃,初苒有些狼吞虎嚥。猛一扭頭,不知何時蕭鳶竟轉過身來,倚在枕上看她。
「咳、咳……」初苒一陣嗆咳,順手端起茶盞就喝,好容易喘過氣來,卻見蕭鳶盯著她的手,眼角的笑意更深。
初苒這才驚覺自己喝了他的茶,忙訕訕地笑著放下:「先生可是要茶?盼兒給先生換只盞子。」
蕭鳶眸色幽深,臉在燭影裡半明半暗,修長的手指不知從哪裡拈出一只寸許的玉瓶,放在軟榻前。「頭若還痛,就用它揉揉。」說罷,又返身朝裡躺下。
初苒摸著後腦勺愣了半晌。玉瓶溫涼,握在手中,她想起在慈安堂第一次見他時的模樣,思緒凌亂,「這人莫非人格分裂?白天夜裡兩個樣兒……」
☆☆☆ ☆☆☆ ☆☆☆
車隊每日亥時宿下,寅時出發。
一到車隊休整之處,初苒就整理車廂,更換熱水吃食,焚點淨香,做的盡是莫青原先的差事。
「怎好讓姑娘做這些事情。」莫青不好意思地又是躬身又是作揖。
「我與你是一樣的,怎麼就不能做?」初苒微笑。
「姑娘可別這麼說。」莫青朝遠處偷瞄一眼,又拱手道:「饒是這樣,一會兒還得勞煩姑娘,筆墨都在那只梨木櫃子卍字扣兒的抽屜裡,待會兒主子爺要用。」
初苒笑著點頭,同情地看著莫青飛奔而去的背影,心有所動。莫青不過也就是個十六、七歲的孩子,比她的實際年齡還要小些,她又何必做些矜貴小姐琉璃心的模樣。何況她還欠了蕭鳶許多人情,若是趁著眼下多做些事,日後離開時,也走得安心。
初苒這般想著,心中的悶氣消下去不少,天氣都格外晴好。
待蕭鳶上了馬車,初苒規規矩矩的據在一角,替他安好筆墨,又將莫青遞進來的一只漆木匣子搬到矮几上抽開,匣子裡頭分了數格,擱著各色信函與錦盒。一連兩個時辰,蕭鳶都在拆閱覆函,初苒跪坐在一旁研墨奉茶,半日下來,累得腰痠頸僵,蕭鳶卻不曾有半刻休息。
中間莫青又送進來一匣,將蕭鳶批好的回函,用先前的匣子分類裝滿後取走。初苒見了也學著樣子,將回函按不同的漆封分類碼在格子裡。
又是半日,見木匣漸漸盛滿,初苒輕聲問道:「先生,可要喚莫青進來?」
蕭鳶瞥了一眼碼得整齊的匣格,停筆問道:「盼兒認得字?」
初苒點點頭又搖搖頭,蕭鳶也不深究,一邊用手中的筆管指指車門,一邊隨口說道:「日後得了空,再好生教妳。」
初苒闔上匣子,正欲去拉車門喚莫青,卻又聽見淡然的聲音從身後傳來。
「哦,在下忘了,盼兒姑娘不喜習字。姑娘心中所求,乃是織繡之技。」蕭鳶手中批閱,口中調侃:「『織霞』是難了些,不過若論繡藝,雍都府裡還是有人可與『天人』比肩的。待回了雍都,在下定為姑娘謀一位好師父。」
不必回頭,初苒也可以想像那人令人嫌惡的嘴臉。織霞,織霞!不戲弄她就不舒服是吧!丫頭也有尊嚴,妥協也有限度!初苒再懶得理會什麼勞什子信匣,板起臉一聲不吭的坐回角落。
蕭鳶那廂筆硯、茶盞悉悉索索響個不亦樂乎,後來甚至還有一兩聲愉悅地低笑。
初苒愈發氣得閉起眼睛,佯裝打瞌睡。
旅途漫漫,一連數日顛簸下來,初苒漸覺吃力。
蕭鳶日日皆是數不清的信函,逢他在燭下凝神批閱時,初苒就會想起紫宸殿裡的元帝。
兩人年紀相仿,白日裡並不覺得什麼,獨到晚間,蕭鳶去了那些霸道的浮躁之氣,兩人的眉目神情就極為酷似。起先,初苒還只是在心中臆想,如今看到蕭鳶日日所理的事務,只怕他的身分不是皇子就是諸侯。
所謂伴君如伴虎,初苒強打起精神,謹言慎行了許多。
又值一日,秋陽灩灩。
莫青在窗下稟道:「主子爺,涿泊湖到了,可要停一停?」
蕭鳶欣然下車,初苒也好奇的跟了下去。
車隊停在稀疏的林中,遠處是一片開闊的翠藍澄淨。
何謂碧水藍天,何謂秋高氣爽,放在這當口再合適不過。
可是剛靠近湖邊,初苒就打了一個冷顫,這冰藍的湖水竟比看起來還要寒意浸人。
跟在後頭磨蹭了一會兒,蕭鳶、莫青一行漸漸走遠,初苒索性偷偷溜回馬車,伸展了身子夢周公。
待得蕭鳶回來時,推開車門,就見初苒枕著胳膊睡得香沉。微凹的眼簾緊闔,似是累極,細密的長睫在粉頰上投下一道好看的陰影,平日裡緊抿的小嘴此時舒展的翹起,唇上一抹溫潤的櫻色。
蕭鳶眼神幽暗,輕輕闔上車門,復向湖邊走去。
初苒一覺好睡,醒來已是紅日偏西,車隊竟在涿泊湖耽擱了半日。
眾人都在林中歇息,獨莫青抱著一件斗篷立在湖邊,初苒好奇地過去詢問。
莫青無奈地抬起下巴指指湖心,「主子爺還在游湖呢。」
初苒循著莫青的目光看過去,竟見蕭鳶赤身在湖水裡游弋,不禁驚道:「這怎麼可以?現下已是深秋,湖水又冰寒,哪有你家主子這樣游湖的?」
莫青耷拉著頭,小聲咕噥道:「主子爺的心思誰能曉得?先還是在湖邊呆坐的,後來就游到湖裡去了。」
初苒風寒初癒,深知其中苦楚。這個時代風寒重了也是可以死人的,何況他們尚在途中,也不曉得隊伍裡可有大夫。
一陣水聲,蕭鳶已到了岸邊似要起身的模樣,初苒忙背過身子,低聲和莫青說道:「你快去伺候你主子爺,我去煎碗薑茶來,給他驅寒。」
「薑茶?給主子爺?」莫青張大了嘴。
初苒也不多說,低著頭急急地嗯了一聲就走開了。
一會兒工夫,初苒端了滾燙的薑茶回來,湖邊卻不見了莫青,只有蕭鳶獨自躺在大石上。
赤裸的腿腳不曾著鞋襪,勁瘦的手臂遮在眼前,衣衫只隨意攔在腰間,露出胸前大片蜜色的肌膚和寬闊的肩背。這這這!簡直是赤裸裸的誘惑……
初苒低頭背身站在樹後,臉頰燒得厲害不說,手中的茶碗也磕磕碰碰,哆嗦個沒完。
極品男色啊有木有!再看,再看我就把你吃掉……不,不對,她還很稚嫩很純潔。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南無救世觀世音菩薩……
天色漸暗,蕭鳶披著濕髮坐到火堆前,依舊衣襟大敞。初苒呆看著莫青提來酒罈,蕭鳶飲到第十碗時,她終於有些覺悟了。
好吧,是她多餘了。
男人和女人本就是兩種動物,男人在寒浸浸的湖水裡泡過之後,幾碗烈酒就是良方,她這樣的小丫頭卻會因為風餐露宿就發熱生病,還被迫寄人籬下養病,現在連自由也弄丟了!真是沒天理啊!
暮色降臨,眾人在林中用過晚飯,又徐徐出發了,今晚要連夜趕路。
初苒坐在車內迷迷糊糊地打著瞌睡。半夜時分,卻發現蕭鳶額上細汗淋漓,雙頰潮紅。
莫非還是發熱了?初苒輕喚了幾聲,也不見他回應。
拿帕子替他拭了額間的細汗,初苒又用手背試了試溫度,倒是不燙。難道是做夢魘住了?
正兀自不解,覆在蕭鳶額上的手卻被他一把握住再抽不回,初苒掙扎數次,卻被抓得更緊。看那人眼簾深闔睡得極沉,並不似作偽,初苒只好忍著手痛,跪坐在軟榻前由他握著。
馬車仍是搖晃,蕭鳶漸漸舒展了眉頭,面色也好轉起來,初苒睏倦地靠在一旁的矮几上打盹兒。
清晨,蕭鳶醒來時,睜眼便見初苒安詳的睡顏,愕然之餘,手中一握柔軟膩滑,笑意不禁從他唇角直達眼底。
溫玉在側,蘭氣如氤。蕭鳶揉捏著掌中柔若無骨的小手,想起初苒昨日在湖邊羞怯的模樣,竟忽然覺得車內燥熱氣悶起來。
幾度生死,幾度化險為夷,眾人的命運因她改寫。
艱難險阻,是誰錯身而過?又是誰不離不棄,攜手永世,看盡山河……
萬九兒《美人搏命》全五冊/8月22日、29日好戲連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