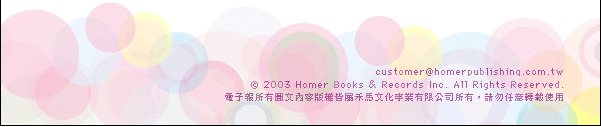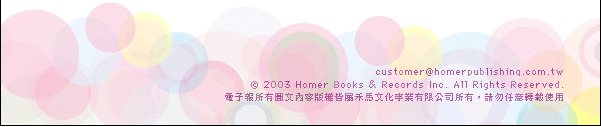|
連載專區:
蔡小雀/宰相門前好孕來
★★★
這一夜,雨打芭蕉。
文無瑕坐在上書房外間一隅,修長大手持毫舞墨,專心一意地在代擬的奏摺上走筆如飛。
片刻後,他停下筆,揉了揉微痠的手腕,一抬眼,這才發現半個時辰前,那位妖豔非常的清皇明明還坐在另一頭,煞有介事地捧起摺子,好似看得還挺起勁兒的,可才一下子沒注意,龍案後頭已然人影不見。
「唉。」他也不知該嘆息還是該笑好。
想必皇上又偷偷溜回寢殿找貼身大宮女阿童姑娘去了。
他經常在想,皇上當初獨排眾議,拔擢他為萬年王朝史上最年輕的宰相,不知是不是看中了年歲相近的他,不似那些年高德劭、白髮蒼蒼的老臣那般冥頑不靈、食古不化?既是年輕人心思敞亮開懷,自然也就不會對皇上獨寵宮女一事,做出諸如「大驚小怪,當堂死諫」的那等閒事來。
可就算真是這樣,皇上也不該在他面前躲懶躲得如此光明正大,還索性拿了臣工當長工用啊!
搖搖頭,文無瑕也只能摸摸鼻子自認倒楣,繼續代皇帝擬下要示以路州諸府縣官員們,關於水患的種種措施方策。
……路州水患,缺土包糧米,當可先自靈州調之。慎防大水過後疫病四起,宜速至蕪州召募郎中藥草,蕪州石城有草名「忘憂」,治發熱尤為甚好……
筆尖驀然一頓,在綢絹上落下了一點墨漬,恰似淚痕。
「忘憂,這藥名還真特別……」他嗓音沉靜溫雅地喃喃,似沒意識到自己脫口而出什麼。
亮晃晃的燈花陡地一爆,文無瑕回過神來,又復專注揮毫書寫,細細交代下去。
雨聲淅瀝瀝地落下,在靜靜的夜裡分外清靈好聽,只是隨著驟雨起的濛濛霧氣,朦朦朧朧地教眼前景物怎麼也看不清……
★★★
顛鸞倒鳳第一式──說那以退為進,偏俏生生欲拒還迎。
沒有綠蔭遮日,小溪潺潺,京城的晚春初夏,著實教人吃不消啊。
夏迎春自袖裡掏出一方帕子抖了抖,朝香汗淋漓的額頭胡抹了一把,略略喘了口氣,揉揉有些作痠的腰,仰頭瞇起眼望著面前兩扇朱紅重門,高懸的匾額上頭有龍飛鳳舞的三個古墨大字──文相府。
謝天謝地,終於到了。
但見她彎眉如畫,明眸閃閃,絳唇輕點,未語先笑,髮際綰得嫵媚非常的飛燕髻斜簪著銀步搖,嬌豔臉蛋掩不住的興奮歡喜,一身婦人裝束,寬袍長襬搖曳生姿,通身上下有說不盡的風流意態,只是腹間肚兒隆起,顯是身懷有孕,且看模樣也該有五、六個月大了。
方才乘坐的馬車已然駛遠,她腳邊就放著只箱籠,臂彎勾著的包袱細軟拎久了也有些沉了……該是時候了。
「這兒是文無瑕府上吧?」她對從剛剛便疑惑地盯著自己的兩名守門家丁問道,燦然一笑。「他在不在家?」
「相爺進宮了。」家丁甲遲疑道:「這位夫人若是想求見我家相爺,應當事先三天前投拜帖才是。」
「這位小哥兒說笑了。我找自家相公,還得投什麼拜帖?」夏迎春噗地笑了起來。
此話一出,不啻平地起了聲旱天雷,轟得文府兩位家丁幾乎眼珠突出、下巴掉落。
「啥?!」
「我叫夏迎春,是你家相爺文無瑕孩子的娘親。」她眉眼彎彎,唇兒上揚,好似沒瞧見四周那些越圍越多,集震驚、痛心、惋惜、嫉妒之色俱有之的騷動人群,兀自笑嘻嘻道:「所以,照常理推論,我該是你家夫人。」
兩名家丁還未從錯愕中清醒,那些時不時在相府門前閒晃、千方百計想和文無瑕來個「不期而遇」的仰慕者登時炸鍋了──
「妳妳妳……胡說八道個什麼東西?」
「文相溫文爾雅、清朗如玉,向來知書達禮、潔身自好,從不見有什麼桃色緋聞,妳這瘋婆娘怎可誣衊我們心中天人一般的文相?」
「就是就是。想文相驚才絕豔,乃名滿天下第一翩翩才子,更是萬年王朝有史以來最年輕、最賢名遠播的有德宰相,豈是妳一個無知婦人可攀附得?」
眾人鼓譟著,像是恨不得將這名膽敢染指他們心目中絕代風華偶像的輕薄女打殺於當場。
夏迎春原本歡喜的笑容從凝滯,不悅,抽搐,到火大。
「我說你們是夠了沒!」
她一聲河東獅吼,當場震得在場眾人噤聲不語。
「你們是文無瑕嗎?你們姓文嗎?你們住相府嗎?你們是文家三大姑四大嬸八大叔嗎?」她眸光厲色一掃,眾人紛紛低下頭去。「本娘子馬車吐了一路,好不容易晃到京城來,是找文無瑕給我肚裡的孩子負責的,是要問問他吃完了就跑,算什麼英雄好漢。在場和文家沒半毛干係的閒雜人等,統統閃一邊去!」
眾人呆了半晌說不出話來,最後也只得做鳥獸散,但嘴上仍不忘嘀咕──
「文相何辜啊!」
「居然被這等煙視媚行、狼虎之姿的惡女纏上……」
「明明是帖狗皮膏藥,還敢妄想黏得住文相那等極品君子……」
「聽聽,她那意思是指文相始亂終棄不成?嘖嘖,就憑她這德行,只怕哭著跪求文相碰一根手指,文相都嫌骯髒哪!」
夏迎春氣得微微發抖,肚裡寶貝兒也似激動不已地頻頻伸拳踢腿,惹得她只得強按怒火,好生搓揉安撫了肚子一陣。
「沒事兒沒事兒,這閒人閒話到處都有,咱不氣,不氣啊!」她深吸一口氣,再擠出一朵燦爛親切笑花,對著兩名神色陰晴不定的家丁道:「既是他不在,那府裡可還有長輩或是說得上話的人在?」
家丁甲和家丁乙面面相覷,只覺頭大如斗,冷汗直冒。
★★★
上書房
本與皇帝玄清鳳說那幽州兵佈圖,說著說著,不知怎的話題又到了皇帝不可言說的心頭寶阮阿童身上,文無瑕看著皇帝還在那兒死鴨子嘴硬,纏呀繞呀地就是說不清楚自家心事底蘊來,不禁暗暗一笑。
果然下至販夫走卒,上至帝王將相,但凡一牽扯到這「情」字,便極難有個明白人。
他搖了搖頭,本想寬慰皇帝幾句,稍稍解了聖上心憂,恰時一個熟悉的嗓音自上書房門口響起。
「皇上,文相大人,奴婢有要事稟報。」在門口的阮阿童面色有些尷尬,像是有口難言。「文相大人,貴府管家方才遞了牌子,入宮急尋大人回去。」
文無瑕眉毛微挑。
管家譚伯向來沉穩,今日是什麼急事非得遞牌子進宮?
「愛卿家中出了什麼事嗎?」玄清鳳逮著機會似的精神一振,立刻還以「反打探」顏色。「好阿童,說給朕聽聽。」
阮阿童猶豫地看了一臉茫然的文無瑕一眼,吞吞吐吐道:「奴婢見那管家神色驚急,沒有多問一二。大人可要先行回府料理家事?」
「這……」文無瑕疑惑地蹙起眉心。
「家事?」玄清鳳頓時樂了,笑得眉眼彎彎。「快說快說,朕最喜歡為臣子解決家中疑難雜事了。」
雖是阮阿童對他頻頻暗示,然而文無瑕一向自詡潔身自好、君子磊落,絕無不可對人言之事,因此也正色道:「阿童姑娘請直說無妨,若管家所言乃尋常瑣事,盡可不必相理。再多大的家事,也大不了國事去。」
「就是就是,阿童莫再賣關子了。」玄清鳳催促,滿眼熱切得亮晶晶。
「貴府管家前來急請大人回府,說是……呃……」她清了清喉嚨,訕訕然道:「有名女子萬里尋夫至相府門前,大腹便便,當街控訴大人……始亂終棄。」
饒是溫潤如玉的文無瑕素來氣定神閒,鎮定功夫非常人可及,聞言也不禁微微色變。
「哎呀呀呀!」玄清鳳樂不可支,拍案哈哈大笑出聲。「愛卿啊愛卿,朕萬萬沒想到愛卿一世清名,居然也會幹下此等人神共憤、世所不容的──」
皇帝話還沒說完,就被文無瑕一記冰若寒霜的眼刀給砍斷了。
「皇上,臣雖不才,自認半生以來嚴從聖人之道,從未有過任何行差踏錯的逾越之舉。」他面上微笑仍在,眼神已是冷了下來,周身氣勢令人不寒而慄。「今日之事,請容微臣先行回府探究處置個分明,再向皇上詳稟,如何?」
就是最後兩字的加重語氣,令向來逮著了機會見臣子鬧笑話便不依不饒的玄清鳳也不好意思再吐他的槽,反而擺出一副「哎呀!難道朕還信不過愛卿你嗎?」的誠懇神情。
──別以為他看不懂皇上看似誠懇關懷、實則幸災樂禍的眼色。
只是匆忙之間,他也無心再反將皇上一軍,只速速告退而去,留下笑到嘴角疑似快抽筋的玄清鳳和一臉好抱歉的阮阿童。
縱然疾步走向宮門,髮束玉冠,足踏雲靴,一身繡金白袍的文無瑕,依然身姿挺拔如竹,在和三三兩兩朝臣擦肩而過時,也不忘拱手回禮,閒然地略叮囑了一二句。
無人看得出他氣息微滯於胸,只當是尋常時候,下了朝要乘車回府。
一出宮門口,文無瑕對立刻迎上前來的管家微擺手,止住管家的急急稟告之言。
「回府再說。」
「是,相爺。」
★★★
匆匆回到相府,文無瑕向來俊雅的臉龐已抑不住一抹罕見的慍怒,直到腳步停在招待來客的雁堂前,他兩道好看的眉毛皺了起來。
咳咳,好重的脂粉味。
一時間,他突然有種抬腳入內之後,便「是禍非福不死也傷」的莫名警兆感。
稍稍穩定下心神,他臉上神情恢復一貫淡然,再舉步時,已是氣定神閒從容不迫。
踏入雁堂內,首先躍入眼底的便是那一張笑得燦爛卻陌生的臉龐。
「守諾,果然真的是你!」
文無瑕一愣,所有準備好的禮貌問句在腦中瞬間消失無蹤。
在管家和婢女僕從們驚掉了下巴的瞪視中,一股帶著濃濃香風的身形如餓虎撲羊般飛奔入他懷裡,死死地攀抓住他不放──
像是歷經了千山萬水,像是走過了風霜雨雪,像是數過了無數無數個期盼煎熬的心跳,終於再度找回了他……
夏迎春把臉埋在那熟悉的胸口,淚水恣意奔流,緊揪著他腰際衣衫的手指顫抖著,嘴裡已是又笑又罵的嚷了起來。
「我還以為這輩子再也見不到你,真真想死我也嚇死我了……」
良久之後,情迷意亂激盪難抑的夏迎春終於感覺到了懷裡這具溫暖胸膛的拘謹僵硬。
她迷惑地抬起被淚水糊得花貓似的臉蛋,望入一雙清冷平靜的眸子裡。
「這位夫人,還請自重。」文無瑕伸手扶正她,不著痕跡地後退一步,睫毛低垂,掩住了所有的尷尬震驚不快。
就連遭受如此「非禮」,他也還是一派謙謙君子氣度。
「你、你推開我?」她眼裡閃過無從掩飾的慌亂痛楚,有些受傷地喃喃,「你不高興見到我?」
能高興嗎?
「失禮了,可妳我並不相識。」他輕蹙眉心,隨即舒展開來,神態斯文清朗,嘴角泛著禮貌微笑,然而通身上下卻透著一股令人無法逼視、不容抗拒的守禮疏離。
尤其,當他的目光落在她隆起的肚腹時,更是掠過了一絲……
不贊同?鄙夷?
夏迎春忍不住打了個寒顫,好似在他眼前的自己,是個多麼厚顏無恥、不守婦道的輕薄女。
「怎會不相識?你睜大眼睛看清楚點我是誰!」她急急道。
「這位夫人妳認錯人了,本相姓文名無瑕,非妳口中稱『守諾』之人。」
「我後來才知道你是文無瑕。」她嗓音微顫,隨即倔強地抬起下巴。「可你還是我的守諾!你就是我的守諾,從頭到腳,連寒毛都是,就算化成了灰我也認得你。」
「這位夫人,倘若妳有什麼不能對人言的困難之處,本相自可盡力協助妳,可像是這等胡亂攀誣之事,還請夫人切莫再為之。」他眸底嚴峻一閃而逝,「須記自重人重。」
對著他那清冷的目光,拒人於千里之外的語氣,夏迎春的臉色登時慘白,有種恐懼竄過眼底。
「你……你真不記得我了?」
短短數字相詢,個中淒涼之意,沒來由地令文無瑕心頭一撞。
他定了定神,開始仔細地、用心專注地凝視端詳著她,由頭至腳,眉眼鼻尖唇瓣下巴……最後,帶著一縷歉然地輕嘆。
「對不住。」他搖了搖頭,語氣篤定地道:「文某確實與夫人素不相識。」
看著他澄澈清亮卻疑惑陌生的眼神,夏迎春頓時像捱了一記悶棍,身子晃了下。
文無瑕本想伸手扶住她,終究還是戒於男女大防,僅是瞥了一旁看傻了的婢女一眼。
婢女得自家相爺示意,只得上前攙扶住了這個半路胡亂認夫的大膽無知婦人。
夏迎春愣愣地被扶著,一動也不動,一顆心卻不可遏止地劇烈顫抖了起來。
他看著她的樣子,眼神帶著淡淡的好奇、迷惑及不解,卻又無比的坦然無畏,完全就是看著一個素眛平生的人……沒有人的眼神可以偽裝得這麼真實、這麼成功。
難道他不是始亂終棄,不是狠心相負,他……他是真的不記得她了嗎?
怎麼會?怎麼可能?
她沒有說話,沒有反應,只是水靈靈的眸子漸漸泛起淚光,似有說不出的淒惶、悲傷。
她沒事吧?
文無瑕胸口一緊,心底泛起一絲憂思,卻也僅僅止於人與人之間基本的關懷而已。
「不……」她緩緩地閉上了眼。
他一怔。
但見她深吸了一口氣,忽地睜開了眼。
他還來不及開口問點什麼,下一瞬間,額頭已被一股重力狠狠地掃中了!
「叫你忘了我!」但見一個毫無氣質的嬌小孕婦跳起來狠狠巴當朝宰相的頭,身姿之靈活,動作之老練,令在場眾人為之震驚錯愕。「我叫你忘了我!就你這豆腐腦記性還敢忘了我?宰相是嗎?我看根本就是蠢相,你那頭銜是花錢買來的是吧?」
文無瑕這一生從未遇過如此怪異荒謬「凶殘」的遭遇,風度翩翩的儒雅公子被不由分說亂打一通,雖說不到抱頭鼠竄那麼難看,也是措手不及得節節敗退。
「這位夫人……」被暴打中,既驚且惱的他試圖抓穩她的雙手,一方面阻止她繼續行凶,一方面也唯恐她傷著了自己──話說回來,她到底有沒有自覺是孕婦?她又哪來這般理直氣壯對他痛下打手?
「放開我們家相爺!」
「大膽!」
「妳、妳快放手!」
奴僕們驚怒交加地就想衝向前拉住她,可沒想到她雖然挺著個肚子,動作卻十分靈活,他們又怕一個失手拉扯衝撞到她「手中」的相爺。
「放?放你娘的狗臭屁!」最後,夏迎春終於追打累了,手扶著腰氣喘吁吁地停下,嬌容怒色半分不減。「本姑娘只用手,還沒棒打薄情郎,已經是很給他面子了!」
「大膽瘋婦,竟敢對我家相爺無禮!」相府的僕奴們迫不及待圍上來要押住她。
「都下去。」文無瑕忍著滿頭滿身的疼感和狼狽,喝退眾人後,清亮溫和目光倏轉而銳利十分。「這位夫人,君子動口不動手。」
若非看在她是個孕婦,又口口聲聲為尋夫而來的份上,他又何至於再三忍讓這種種冒犯不敬之舉?
「夫你姥爺的!我叫夏迎春!」她怒氣騰騰地瞪著他,「好呀你,是不是一句『忘了』就想打發我?到底你當我是白癡還是把自己當白癡?不過看你這表情這神態這眼色,分明就是把我當白癡,才以為用這種老梗賤招爛理由就能把我撇清得一乾二淨了是吧?」
他目瞪口呆地看著她,一時間也不知道該是驚奇還是欽佩好。
連換氣都不用,便能談言吐字如行雲流水,真真非常人所能也。
「喂,你!」夏迎春惡狠狠地對他一勾手指頭。「過來!」
文無瑕回過神來,俊雅臉龐一臉警戒,腳下不動。「夫人有話在這兒說便好,文某就不過去了。」
「別以為站離我十步遠我就巴不到你。」她瞇起眼,殺氣橫溢。「信不信憑本姑娘一隻繡花鞋也可以百步穿楊、取你首級?」
「咳咳!」他被口水嗆到,這這這……世上有這種女人嗎?她到底是自哪個山寨奔下來的母大王?
所謂女子,當溫婉知禮,雍雅大方,談吐宜人,豈有她這樣的?
「再說一句不認識我試試!」她橫眉豎目。
「文某確實不認識夫人。」他嘆了口氣,正色道。
「有本事再對著我肚子發誓說你不認識!」她眼角抽搐。
「文某發誓確實不認識夫人。」他書生意氣也擰上來了。
夏迎春瞪著他,一個呼吸、兩個呼吸、三個呼吸的辰光,然後慢慢磨起了牙齒猙獰一笑,笑得他莫名腳底發冷。「不、認、識?」
文無瑕吞了口口水,下意識後退了一步。「呃……」
「行!」
行什麼?他還來不及反應過來,就見她一把扯下了腰帶,麗色衣衫半鬆開來,微露出雪色裡衣襯裙。
「夫人……請自重。」文無瑕清俊臉龐泛紅,立刻背過身去。
「好!既然不認識,那我和孩子死了也不關你一毛干係!」她咬牙切齒,陰惻惻嗓音裡依然聽得出滿滿的傷心。
背對著她的挺拔身影一僵,還是沒有轉過身來,顯然深不認為她當真會上演那更老梗的「一哭二鬧三上吊」戲碼。
直到後方傳來椅凳翻倒的不祥聲響,文無瑕心一緊,急急回過頭來,一看之下大驚失色。
「喂喂!夫人、姑娘,妳……」他慌得七手八腳將她掛在半空中的身子抱下來,一顆心跳得如擂鼓,驚得面色發白。「有話好說,妳何至於此?」
「咳咳咳……」夏迎春邊嗆咳邊喘氣,淚水都咳出來了。
這無情薄倖的大混蛋,他這是救人還是殺人哪?她本來都算計好了雙手緊攢著腰帶邊緣,只是把脖子那麼虛虛一掛做個樣子,可被他雙臂往她腿上緊抱一拖而下,生生勒得她差點吐舌斷氣。
他根本就是故意的吧?!
「妳還好嗎?來人,快叫大夫──」
喉嚨痛得似火燒,耳際又被他的吼聲震得嗡嗡生疼,夏迎春索性假作眼皮一翻,暈了過去。
……想一聲「忘了」便攆本姑娘走,書呆相爺,您還嫩點兒哪!
★★★
顛鸞倒鳳第二式──羞逗櫻桃點點紅,翻倒了葡萄架。
想她夏迎春,可是石城唯一一間青樓「怡紅院」的當家老鴇,自幼承繼家業,見過的花姑娘和龜公、尋歡客沒有一千也有八百,打小她便是窩在床底下聽著上頭嗯嗯啊啊咿咿呀呀聲,一邊啃包子一邊畫春宮圖長大的,多年來培養出了她無比堅韌的心性,極度厚實的臉皮,以及沒有尺度、沒有羞恥的本領。
是故,才能以十五歲清白佳人之身,兩年來率領一干花紅柳綠姑娘,在南來北往商潮熱點的石城小鎮上站穩腳步,為眾多商客提供最溫馨最火辣辣的銷魂服務。
可這樣一個恣意不羈、無形無狀的她,偏偏栽在了他一個溫雅可人的文弱書生手裡。
是可忍,孰不可忍。
夏迎春在心底冷笑著,緊閉雙眼,面上還是裝作人事不知的樣子,只豎起雙耳聆聽四周動靜。
「大夫,她怎麼樣了?」那個一貫文雅的聲音透著一絲關切。
死傢伙現在裝什麼純情裝什麼關心?剛剛想跟他相認、需要他關懷的時候都幹啥去了?
「咳,回相爺的話,夫人是肝火旺盛了些,沒有大礙,吃幾帖藥靜養幾天就沒事了。」老大夫聽似正經八百的醫囑裡,完全掩飾不住想打探緋聞的熱切。「敢問相爺,這位夫人是您的……」
「大夫這邊開藥!」管家凶霸霸的聲音橫插一槓,顯然自家相爺今日被侮辱被誣衊的程度已經到達他無法容忍的地步。「請!」
夏迎春心中的冷笑更深了,當這樣就可以隻手遮天了嗎?
然後又是一陣細碎的腳步聲離去,屋內恢復靜謐,靜得彷彿只有聽得見她自己的心跳聲。
耶?都走了?
她小心翼翼地睜開一隻眼睛窺看,直勾勾對上了那雙若有所思的深邃黑眸,駭得她瞬間瞪圓了雙眼。
「你……」不是也出去了嗎?
「夏姑娘,妳醒了。」文無瑕面色平靜無波,很是鎮定。
「呃……欸。」對上眼前這張帶著濃濃書卷氣息的清潤如玉俊容,一時之間,她的心亂跳了兩三下,往日熟悉的著迷癡戀又如大網般當頭罩了下來。
夏迎春,爭氣點!現在可不是美色當前,暈頭轉向的時候!
就在她暗中恨恨唾棄自己的當兒,那柔和如月華的嗓音又在她耳畔響起。
「妳冷靜些了嗎?」他目光溫和地看著她。
……就好像她方才十足是個潑婦,而現在好不容易終於正常點。
她臉色瞬地一僵。
就憑這氣死人不償命的溫和問法,她完全可以板上釘釘的確定他便是她的守諾!這世上除了守諾之外,還有誰有這種柔和溫雅的語氣和真摯就能活生生氣死人的功力?
雖然,夏迎春承認自己剛剛又打又鬧又上吊的行為確實過激了點,可這都是拜誰所賜啊?
「哼!」她自鼻孔重重哼出聲。
見她就算不說話也是副張牙舞爪的凶橫樣,文無瑕嘆了一口氣。
「女子當以幽嫻貞靜為好。」
屁!她怒極反笑。
「尤其夏姑娘現在身懷有孕,更該潔身自愛,顧惜自己的德行與身子……」文無瑕看著她,說著說著,眸底的不贊同之色漸漸演變成尷尬。
他臉紅個什麼東西呀!
夏迎春完全沒有意識到自己現下因生氣,還有方才的「上吊」過程,致使衣衫半褪,先前他閉上眼睛幫她蓋好了被子,卻又被她氣極坐直起來的動作,導致該遮的地方越發遮不住,不該露的露得更開。
她只顧著火冒三丈,「你都不認我和孩子了,我還潔身自好個鬼?」
他把目光別向他處,輕咳了一聲。「夏姑娘請先整理好衣衫。」
她一怔,低下頭,這才看見自己露出了一抹桃紅色肚兜,臉微微一熱,忙攏緊了衫子,偏還是嘴硬。「全身上下都被你瞧過了,還裝什麼正直好青年,呸!」
雖說夏迎春平素是個大膽的,可每每一對上他這個溫文正直的書生郎,她骨子裡僅存的少少羞恥心就會冒出來作祟。
「夏姑娘,妳──」他這下臉不紅,而是一陣青一陣白了。「文某並非妳口口聲聲提及的那位守諾兄,姑娘真的認錯人了。」
「你說認錯就認錯?」她雙手抱臂,挑眉恨恨一笑。「你全身上下都被我摸透了,哪兒硬哪兒軟哪兒有胎記我都知道,敢不敢當堂驗證?」
文無瑕瞪著她,又是尷尬又是懊惱又是不知所措。真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
「夏姑娘,要如何妳才願意相信,文某的確不是妳要找的那個人?」他極力維持住最後一寸理智鎮靜,微蹙清眉看著她。
「脫光了給我指認,我就信。」她一昂下巴,笑得好不嫵媚張揚。
「妳妳──男女有別,豈可赤身露體?」他那張俊雅臉龐漲紅一片。「禮教何存──」
「不然我脫光了給你指認?」夏迎春見他這副「嬌羞可欺」的模樣,色心又起,不由露出狼虎邪笑。「選一個,你脫?還是我脫?嗯?」
「姑娘請自重!」文無瑕最終還是羞極反惱,霍地站了起來,當朝宰輔氣勢凜然表露無遺。「我朝王法律令有載,白晝當街淫穢者,不論男女,按律鞭五十,發配邊疆;失貞犯行失德者,杖責八十,發賣為奴──」
「行了行了。」她打了個呵欠,揮了揮手。「我信了你是當朝宰相行不?」
他餘下的話全噎在喉頭。
「我餓了。」她懶洋洋地看了他一眼。「要鞭要打也得等我填飽肚皮再說,我不吃,肚裡還有一個等著吃呢!」
文無瑕臉上一陣紅一陣白,目光複雜至極地盯著她,也不知是惱是氣還是無奈,她就相準了他決計不忍心刑責一個大腹便便的女子嗎?
他有一剎那的衝動,頗想立時翻臉、公事公辦,命人將她速速送至京城提督司衙門裡安置,待日後查明真相再行決斷。
可見她妝點得嬌豔非常的臉蛋上,雖是笑意張揚,眉眼間卻難掩一路風塵僕僕的疲憊之色,一手撫著隆起的肚腹,一手不自覺地輕揉著腰背。
他心念微微一動。
「哎呀!真的好餓啊……」夏迎春偷偷瞄了他一眼,哀嘆。
罷了罷了,古人有云人溺己溺,人飢己飢,就當發一時善念,便留她在府中幾日又如何?
「姑娘,文某這就命人去準備。」文無瑕搖了搖頭,面色不豫地拂袖去了。
夏迎春嘴角緩緩彎起一抹大大的笑容來。
哎哎哎,這麼嘴上古板硬邦邦,實則心軟如豆腐,果然是她的守諾呢!
「不管你是過去的守諾,還是現在的文無瑕,就算你腦子是給驢踢了,又忘了自己是誰,我都不會放掉你的。」她自信滿滿,「我呀,還就不信你真能狠心把我們的過去忘得一乾二淨了。」
雖不知道他為什麼不記得和她之間的種種,但是不要緊,現在她已經來了,只要她夠耐性,軟磨硬泡的時間夠久,終有一日,他一定會想起她的。
★★★
近幾日,文無瑕上朝都有些心不在焉。
儘管依然驚才絕豔談吐有據,依然清朗如竹溫潤若玉,但每當旁的朝臣在稟報的時候,他就佇立在原地發呆,還時不時揉揉眉心、鬢邊,好似疲憊頭疼難當。
忍了好幾天,皇帝玄清鳳還是憋不住了。
「文愛卿,你有黑眼圈嘿!」
文無瑕的臉龐自堆得高高的奏摺上抬起來,神情有一剎那的恍惚,隨即回復銳利。「皇上看錯了。」
「朕眼力好極,百步之外的蟲蟻是公是母,一瞥便知,怎麼會看錯?」玄清鳳絕豔臉上滿是不懷好意的「求知慾」,傾身湊近他面前,問:「如何如何?始亂終棄那回事兒是真的嗎?」
他給了清皇一記冷冷的眼刀,唬得玄清鳳脖子一縮,訕訕然地坐回龍椅上。
「呃,不就問問嘛,朕好歹也是一國之君,掌管天下事……」
「微臣的私事哪及得上皇上的家事?」他不動聲色地道,「聽說,阿童姑娘近日心緒不大好,好似某宮某苑娘娘又衝她撒了好大一頓脾氣。」
「誰?哪個不長眼的膽敢欺負朕的小阿童?」果不其然,玄清鳳龍顏大怒,火氣蒸騰。
順利轉移話題之後,文無瑕繼續低頭整理奏摺,頂多在氣憤跳腳的玄清鳳偶爾回過頭來詢問一二句時,應答個三四字。
寫完收工返府途中,文無瑕嘆了一口氣,俊臉上掠過一抹深思。
皇上是對的,朝政大事處置起來確實比男女私事容易太多了。
一想到回到相府,又得面對那個罵也罵不得、攆也攆不出的刁鑽小婦人,他就頭大如斗。
說來也奇,自己素來極有原則,若心中主意既定,便是威權王霸如皇上也難以撼動他半分決心。
可每當他端肅起臉,開始對她說起女子當克正己身、遵儀守禮等等道理,她便會抱住肚子,一臉吃驚,滿腔悲憤,作出淚眼汪汪指控狀,然後,他也就莫名感到一陣理虧、氣虛,就好像他本該讓著她、護著她,可偏偏他卻欺負了她──
這都是些什麼跟什麼?!
文無瑕揉著眉心,暗道自己定是近來公務太繁重、太熬累,身子有些吃不消,這才連帶使得腦子也不大好使了。
「唉。」他苦惱地嘆了一口氣。
就在此時,轎子猛地停了下來,他連忙抓緊轎窗邊緣穩住身子,沉聲疾問:「怎麼了?」
「回相爺,有人攔轎。」
他愣了下。攔轎?攔轎申冤?
可他又不是京城府尹,也非九門提督,甚至不是刑部之人,這攔轎的未免也太不專業了。
然而文無瑕本著文官之首、國之棟樑的良心,依然傾身向前伸手掀開轎簾。
幾乎是一掀開,他立刻就後悔了。
映入眼簾的是那張這幾日令他頭疼不已的嬌豔張揚笑臉,一手捧著肚子,一手撐著油紙傘,眉眼兒彎彎地望著他。
「妾身來接夫君下差了。」
小廝和轎夫們一片靜默,轎子裡的相爺卻是一頭汗,內心險些淚流滿面。
第一個竄進文無瑕腦子裡的念頭竟是──大街上人多不多?有沒有人看見?
「夏姑娘……」
「呼,站了大半天真是累死我了。」夏迎春不由分說便自動自發爬上轎來,挺著大肚子危危險險的模樣,看得文無瑕倒抽了一口涼氣,慌忙伸臂將她抱上轎裡。
「當心點兒!」他低喝道。
她究竟記不記得自己肚裡還揣著一個?
「哎呀!」她借勢柔若無骨地跌入他懷裡,唇兒偷偷地擦過了他敏感的耳垂,成功地「輕薄」了他一把。
「夏姑娘,妳、妳……」他渾身一震,白皙清俊臉龐倏地紅霞片片,慌亂間,急急將她推開。
「文無瑕!你謀殺妻兒啊?」她嚇了好大一跳,幸虧及時扶住了一旁軟軟的錦墊團墩,抬頭怒目而視。
「對、對不住。」文無瑕匆匆道完歉,驚覺不對,臉色頓時沉了下來。「夏姑娘,妳在我府中百般鬧騰也就罷了,怎能在大庭廣眾之下攀誣辱沒文某清譽?」
夏迎春也惱了,纖纖指尖幾乎戳到他的鼻子去。「我來接自家夫婿下差回家,哪兒錯了?還是你覺得我不夠賢慧不夠漂亮不夠大方,不配在大庭廣眾下喊你夫君,所以丟了你文大相爺的臉面?」
「妳不要指鹿為馬,不知所謂。」他腦袋沉重,捧額哀嘆。「妳明知我指出的重點不是這些。」
「明白,怎麼不明白?」她冷笑,「所謂重點,不就又是那些你不記得我了,我不是你娘子,我壓根是認錯人了叭啦叭啦的狗屁話?」
「夏姑娘──」他幾乎呻吟起來。
「別說我夏迎春色心未盡、淫性又起的在這邊半路認夫婿,胡亂冤枉你,」她一昂下巴,嬌眸熠熠發亮。「我可是有證據的,不信你當場試試看!」
「夏姑娘!」他臉突然又紅了,支支吾吾道:「萬萬不可再提起那些……脫衣……驗證什麼的……罔顧禮教、無視綱紀的渾話。」
「也行。」她很乾脆地一點頭,自信滿滿問:「那我問你,你七個月前是不是去過蕪州?」
「蕪州?」
「對,蕪州石城。」
文無瑕沉思了片刻,謹慎地搖頭。「印象中沒有。」
「好你個──」她恨恨一磨牙,強忍怒氣。「我都已經打聽過了,你七個月前有好長一段時間不在相府裡,是四個月前才回來的。」
「是,文某曾奉皇上聖諭,於回返江南故鄉中途,順道前往路州巡視堤岸諸事宜。」他並無不可對人言之事,光明磊落地坦承。「而後行水路歸京,同行有官員、護衛,都可為我作證。」
「我是在石城水道邊把你撿回家的,當時你一身白袍濕透,狼狽得像水鬼,昏迷不醒,拖你回去的時候還高燒了三天三夜,我家十七八個姑娘和兩名老大夫都可以作證的。」
見她言之鑿鑿,澄澈明亮的眼裡滿是坦蕩之色,致使本是理直氣壯的文無瑕也不禁一時語塞了。
他眨眨眼,有一剎那地迷茫。
真的嗎?他當真曾落水遭她相救,還與她衍生了後續種種情由糾葛?
他記得自己到路州巡視河工的點點滴滴,也記得有幾日大雨疾疾,洪水湍急,他和護衛們三番兩次危危險險地涉水過橋,而路州下游,確實也便是連接蕪州水道。
但他理智上卻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知道,他不曾落過水,不曾認識她,更未與她有過任何交集,因為他腦中對這一切連丁點印象也無。
非但沒有印象,甚至連她的形貌、氣息、聲音都無比陌生。
若她於他而言,當真是至親至愛之人,他又怎麼可能對她的行為舉止、音容笑貌全無一絲熟悉感?
只是文無瑕也不曉得自己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明明行事光明,明明為人坦蕩,可一對上她的撒潑耍賴、胡攪蠻纏,原本的堅持便變得七零八落起來。
好像他原就有愧於心,失了底氣,又怎能與她這般斤斤計較?
可他又愧了她什麼?負了她什麼?
「夏姑娘。」文無瑕甩去腦中莫名其妙的矛盾不可解思維,長吁了一口氣,極力保持冷靜公正道:「妳我各執一詞,這麼下去也不是個辦法。不如這樣,我答應妳會查明此事,而這些時日就請姑娘暫時客居相府中時,謹言慎行,凡事低調,直至事情水落石出之日,如何?」
夏迎春凝視著他,注視之久幾令他有些坐立難安。半晌後,她終於勉強點了點頭。
「好吧。」看在他那麼誠懇的份上。
文無瑕終於鬆了一口氣,只覺冷汗涔涔,濕透了背脊。往常舌戰百官朝臣,乃從容有之、輕鬆有之,還不曾有過這般寸寸艱難的。
「欸,」她伸出青蔥玉指撓蹭他的腰間,笑得好撒嬌好嫵媚。「我餓了。」
「妳……」他心下一撞,背脊僵挺如筆,臉都紅了,也不知是給臊的還是氣的。
「我怎樣?」她燦笑如春花。
妳怎可對我毛手毛腳?
「我怎樣嘛?你說呀!」她俏生生地掩袖笑了,眨了眨眼。「怎麼光衝著人家臉紅呢?」
他勉強忍住了衝動,硬生生地改口道:「不知夏姑娘想吃什麼?」
「魚。」夏迎春眸底浮現一抹似感觸、似幸福的柔軟笑意。「以前你做的西湖醋魚我總嫌酸,可現在一定合胃口。」
文無瑕正想再次解釋那人不是自己,卻見她目光裡暖若春水的笑意忽而蒙上了一層霧氣,素日的嬌豔囂張再不復見。
「真怕以後再想,也吃不著了。」她的聲音低了下去。
他怔怔地看著她,一時間,竟有些恍惚了。
★★★
文無瑕當然沒有當真為了她一番話,就挽袖洗手做羹湯。
因為文家祖訓之一便是「君子遠庖廚」,為此,他更加確信眼前這位小婦人絕絕對對認錯人了,他文無瑕生平從未踏進廚房一步,又怎麼會做那西湖醋魚?
但他還是帶她到城裡以魚鮮馳名天下的「百味樓」,點了一整桌以魚入菜的招牌料理。
文無瑕告訴自己,這桌菜是點來給她肚子裡孩子吃的,不是因為她這個人。
「夏姑娘,請用。」
坐在可憑欄眺望湖面煙波美景的雅座廂房內,他手執玉壺,為彼此斟了蓮子釀。
「哇!」夏迎春眨了眨眼,看花了眼。
糖醋魚,酸辣魚,梅子魚,酸瓜魚,豆釀魚……口味不是清爽的酸甜,便是開胃的香辣,引得她饞蟲大作。
她也不客氣,舉箸便埋頭大快朵頤,吃得噴香。
饒是文無瑕心緒微鬱,可見她吃得這般滿足歡喜的模樣,眼神也不自覺柔和了起來,嘴角輕輕上揚。
雖已做婦人打扮,可見她形容舉止神態,卻還是有三分小女兒的嬌憨稚氣,甚為喜人。
她──真是他私定終身的妻嗎?
他險些被入口的蓮子釀嗆到。
夏迎春夾魚的動作一頓,抬眼關懷地望向他。「怎麼啦?」
「沒什麼。」他搖搖頭,忙放下茶碗,定了定神。
「咦?你都沒吃呢。」她這才注意到他絲毫未動筷,隨即自以為恍然道:「我記得你一向不喜歡這些酸湯辣菜的,還是我讓他們做幾道清淡的來?」
「不。」他清了清喉嚨。「不用了,我不餓。」
「不可能不餓的。」她殷勤熱切地道:「看我,只顧著自己填飽肚皮,倒忘了你在外頭操勞奔波,肯定比我餓得狠了,小二──」
「我說不用了!」文無瑕正惱自己莫名亂了的心緒,衝口而出的語氣裡,嚴峻不悅畢露無遺。
她嚇了一跳。
他頓時意識到自己剛剛的口氣不佳。「呃……」
「也對,想你堂堂宰相金貴身分,自是不屑與我一個小女子同桌共食的。」她看著眼前白袍翩翩,恂恂爾雅,卻已是異樣陌生的他,目光一黯,諷刺之餘有些苦澀地道。
以前守諾都會目光溫暖地看著她吃飯,一面盯著不讓她胡亂挑食,一面細心為她佈菜。
以前她總嗔他管得太多,可現在,他再也不管她了……
因為此刻在他眼裡,她就是個陌生人。
她眸底浮現的傷心令他胸口一緊。「不,我並非嫌棄、不屑──」
「你對我,真的連一點點的印象和眷戀都沒有了嗎?」她直直望著他。
他聞言,沉默不語。
自己雖不願雪上加霜,令她痛上加痛,可怎麼也無法撒謊,拿假話安慰她。
「是啊,你都說你不認得我了。」夏迎春眼神有些恍惚,低聲道:「那就是全都忘光了呀!」
明明都知道,也明明同自己說好了,別把他的疏離戒備太當一回事,那她為什麼還會這麼難過?
一時間,那淡淡的壓抑和悲傷沉沉地籠罩在廂房裡,他們誰也沒說話……
八卦八卦大八卦!
萬年王朝最克己復禮、溫潤如玉的──
文相爺第一次出手就失手!鬧出人命啦~
蔡小雀《宰相門前好孕來》/1月3日/她懷好孕!他走霉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