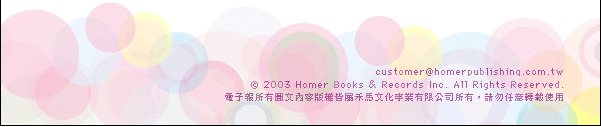人要倒楣,隨時隨地都能碰上衰神,但他呢?
轉頭四處瞧了又瞧,衰神並沒有在他的身邊啊!但為何他就是碰上了這倒楣事呢?
他不過是個甫辦過交接、才上任第三天的新手月老,一隻認分的小菜鳥,安靜地在一旁工作也錯了嗎?別人夫妻吵架干他何事?為何最終倒楣的卻是他呢?
他欲哭無淚地望著手上的姻緣簿,再哀怨地望著一旁吵架的土地公與土地婆。
剛才他才辛苦地牽好了幾條紅線,可就因為他們夫妻吵架,土地婆氣得一掌劈了出去,結果被土地公巧妙地閃躲開來,然後就這麼「精準」地劈中了他甫牽綁上的紅線。
紅線甫接上,姻緣簿上的名字才正要浮出,但這紅線斷了,名字雖是可以完整地看出是誰,但沒全數完整浮現就不算數了。
現在好了,姻緣簿上的位置被不完整的浮字給佔住了,這姻緣不上不下的該如何是好?無故把好姻緣硬生生斬斷,不僅是破壞,要再接續更不是件簡單的工作,那可是要比一般牽綁更困難的。
無故斷了的姻緣可是會改變許多未知的變數,心莫名負了,人莫名死了,都可以是無法續緣的原因;生死有命的定律也會被攪亂,時間與輪迴在他們身上已是沒有任何作用,可說是一場劫難,生死皆由不得自己啊!
「咳咳咳……小老弟,真是對不起了。」土地公摸了摸長長的白鬍子,歉疚地望著月老手上的姻緣簿,也看見了那不完整的部分。
聽見土地公的道歉,月老這才稍稍收起極度哀怨的神情。
雖然牽紅線的工作凸搥了,但至少還有個人可以商量補救的方式,他還不算是太慘了。
「那個……」月老將手中的姻緣簿舉向前,這才想開口問問該怎麼補救才好,但才一開口,什麼都來不及說,土地公便搶先出聲了。
「那個老太婆幹出了這事來,卻一聲道歉也沒給小老弟你,我這就去抓她回來向你道歉……」
「歉」字的尾音還飄蕩在月老的耳邊,眼前滿頭灰白的大老爺卻早已消失無影蹤。
補救的方法不是沒有,但他不過是隻小菜鳥,月老也才當了三天,所有可能的突發狀況雖然上一任月老全都告知過他了,但聽是一回事,真要做又是另一回事了。
兩個讓他上任三天就擺烏龍的夫妻就這麼跑了,他能相信他們真會回來向他道歉嗎?
「可以……不要道歉嗎?」他只要有人幫他補救這些凸搥的姻緣呀!
★★★
在學時,範靖喜便從助理辛苦地半工半讀認真學習起,在學業順利結束後,她也正式成為一名美髮設計師,更和一群好友們共同開設了屬於他們的髮廊,辛苦了幾年下來,在這行也算是小有成就。
團結力量大,這就是他們的座右銘。
努力了好些年,他們自一家店面開始擴店,現在全台灣北中南總共擁有十一間「A Game」髮廊,所以,他們這些老闆兼設計師們很忙,非常的忙。
每個人在固定區域的髮廊間來回工作,並不定時地跨區為助理及準設計師們上課、考試,每天都有一堆行程等著。
能讓她在同一家髮廊內待上長久時間,通常是有預定的行程或是指定客戶。
今天她回到台北的旗艦店內工作,因為接了一位指定客戶。
他是名很特別的客人,讓範靖喜印象十分深刻。
不論哪一家店舖,「A Game」幾位合夥的好友們都有個共同的理念,那就是他們的髮廊不強調時尚前衛,走的是寬敞自然、舒壓療癒的自在生活風;空間設置一律在二樓以上,並以大片強化落地窗包擁整片景觀,完全做到令人身心放鬆的理念。
範靖喜提早來到店裡,先與店長討論有關店裡的大小事務後,這才來到樓下的咖啡專賣店點了兩杯香草密斯朵;一杯是她自己的,另一杯是殷先生的,也就是她的客人。
她的店裡其實提供了許多不同口味的飲品,其中自然少不了咖啡這一項,但幾回的經驗下來,她卻發現店裡提供的飲品不論冷熱他都不喜歡,有的只輕啜一口便不再喝了,有的甚至連喝都沒能喝上一口。
發現她的客人不喜歡店裡所提供的飲品後,她曾試著開口詢問他的喜好,好在下回他再來店裡消費時能夠為他提供,但他只是冷淡地說了聲不必麻煩了。
他不是客套地擔心會為她增添麻煩,而是真的直接拒絕了她。
說真的,當下她真有被人潑了冷水的冰涼感覺,她只是想要讓她的顧客得到完整良好的服務及享受,但他當時面無表情地拒絕了她,那一刻彷彿她做了件愚蠢的事一般。
好吧,她給出了更好的服務品質選擇,是他自動放棄他自身的權益,那麼即便這個客人就此流失了,她也沒什麼好對不起自己,沒什麼需要自我檢討的!
但是,她並沒有流失這個顧客,他仍是固定每個月的第二與第四個星期三會出現在她的店裡,也只指定由她服務。
他仍是無時無刻一身冰冷樣,一樣冷硬的表情不變,除了必要的對談之外,能點頭的絕不開口,能搖頭的,就更不用張嘴活動肌肉。
會替他買這杯香草密斯朵,是上個月某一回他來找她整完頭髮離開髮廊後,當她下樓來到咖啡店裡,卻發現他就排在她前頭。
雖然兩人之間還隔著一位等著買咖啡的客人,但她仍是聽見他點了什麼。
一半牛奶、一半咖啡的香草密斯朵一直是她的最愛,沒想到一向冷冰冰的殷先生也點了它,說真的,那溫潤的飲品跟他這個人真的完全搭不上,有很重的違和感。
那天他轉身離開咖啡店時並未發現她的存在,為了證實他也是喜歡半奶半咖啡的口味,兩個星期後,當他再次準時出現在「A Game」時,她在他坐定後便放了杯香草密斯朵在他眼前。
「請慢用。」她輕聲地說,語調中並未顯露出任何期待他賞臉或者其他情緒,就只是放下杯子,他喝不喝似乎都無所謂了。
但那天他離去後,那杯香草密斯朵只剩空杯了。
所以接下來這兩回,只要是他預約的時間,她都會下樓先買兩杯香草密斯朵,因為這是她唯一能掌握這個客人的小喜好。
他真的是讓她十分困惑的客人,說不上是好客人或壞客人,每每來都只是簡單地說明這回是要剪髮還是洗髮,然後便緊閉著嘴不再多說什麼,像是要從他嘴裡再扳出個字來會要他命似的;說出了目的,接下來全權交到她手裡,也從不擔心她會將他弄成什麼樣子,也從不抱怨她的手藝,這是他好的一面。
但身處服務業,又是專門為人打理門面的工作,她自是希望她所服務的客人可以在離開髮廊前給她一個反應,不論是好是壞──好的,她可以當是讚美;壞的,就當是自我檢討的空間。
而這名殷先生卻從不曾對她的手藝表態過,這才是真正教她在意的部分,也因此對這名安靜得過分的客人有股莫名的在意。
很快地,她帶著兩杯香草密斯朵回到店裡,一向準時的殷先生也正好出現。
範靖喜等著助理為他替換上店內專用的浴袍,並領著他來到最邊角的位子上落坐後,這才端著剛才買的咖啡來到他的身側。
「請慢用。」她將咖啡放在他眼前,便馬上職業性地觀看他的頭髮。
前幾回他都只是來洗頭兼做精油按摩而已,算算時間他也應該要修剪一下了。
當範靖喜專心地觀看著殷侑丞頭髮的當下,她並未對上他的眼,所以再一次很自然地忽略了他眼底一閃即逝的光芒。
眼前的鏡子反射出她那纖細的身影,當她專注力只在於頭髮上的時候,殷侑丞貪婪地將她的身影再次牢牢地深刻在心底。他總是告訴自己,只要這樣看著她就夠了,夠了……
漫長的日子裡,他總是日復一日地悔恨著,他來不及好好地看著她。在失去後,不是不曾想著尋找她,只是一次又一次的失落再失落,他的心痛早已超越言語所能形容的境界了……
當他第一次不經意地經過這家髮廊樓下,與他擦身而過的那張臉龐,是他永遠都不會遺忘的容顏,瞬間他忘了呼吸,時間彷彿是停格住了,周圍的一切變得安靜,在他眼底唯有她,只有她……
他以為他會上前緊緊擁她入懷,落著男兒淚地訴泣被命運莫名擺弄的委屈,然後執著她的手要兩人繼續幸福地走下去……但這一切都只是以為,命運的現實讓他明白他什麼都不能做,甚至只能當個劇場外的觀眾,看著一切就這麼落幕,所以……
現在,她就在眼前,但他已失去了再次擁有她的資格,能夠這樣看著她就足夠了,真的。
小喜,我愛妳,但是……對不起……
「今天要修剪一下嗎?」範靖喜將視線調向鏡子,由反射的鏡面與他對視,這是職業習慣,也是不造成客人與設計師彼此之間壓迫感的方式。
當然,在她目光藉由鏡面與他對上的同時,殷侑丞那充滿複雜情感的瞳眸早已收拾得完全不見蹤影,有的仍是一如往常般的冷肅氣息。
他面無表情地點了點頭,算是給她回應。
一年的時間,不下二十回的接觸經驗,再冷的態度都凍傷不了她了。
因為她知道他一直都是如此待人的,不止是對她,對待任何人都是一樣──冷冰冰的神態,卻不曾無視他人的存在,要她看來,他真的只是不愛笑,不愛說話,不愛與旁人有多餘的交集。
說穿了,他是個孤僻的人……更正,是個孤僻的帥哥。
見他點了頭,範靖喜這才有接續的動作。
「請跟我來。」她側身看著他是否跟上,見他起身了,她這才繼續移動腳步領著他走。
因為是走高級路線的消費層,店裡的設計師包括她自己都有跟影星名人及電視台的合作,也因此店裡的洗頭區共分為兩個區塊:一邊是給一般消費客層使用的,雖然每張躺椅間的距離比起一般店家來說實在大得離譜,但也給了顧客們輕鬆自在、不緊迫的感覺。
但即便如此,廣闊的空間對某些人們來說仍是不夠的,因為他們要的是隔絕人群,完全的隱私空間。
範靖喜領著殷侑丞走入少數的單人洗頭區,那裡原是專門提供給不想受打擾的影視名人們使用,除非有客人特別指定,要不店裡的人通常不會特意帶客人走入這個區塊。
但打從他第一回來到店裡,為他服務的助理由於被他冷過頭的態度給弄得緊張兮兮的,以至於洗頭時不小心讓他耳朵進了水,連眼睛都被洗髮精的泡沫給沾到了。
她沒有開口責備那名助理,而是先向殷侑丞道歉,並接手助理未完成的工作,承諾送他一回免費的精油按摩舒活筋骨。
「由妳為我服務嗎?」
她記得這是他第一回開口對她說的話,那聲調沒有多餘的起伏,只有冷淡平穩的問話,他只要一個簡單的答案,不要無用的贅言。
「我們店裡有專業的按摩師,他們可以讓先生得到完整的舒暢體驗。」她不是推托,雖然身為一名美髮設計師,基本按摩課程學習是一定要會的技能,但再怎樣也比不上專業的按摩師啊!
是的,這裡雖然是髮廊,但順應客人的需求,店內甚至另闢一個區塊作為全身精油按摩的部分,所以他們不僅有頂尖的髮型師,更有技術一流的按摩師。
「不需要。」他冷硬地吐出拒絕的字眼。
夠了,他這是在奢望什麼?不是早已打算每個月偷偷來看她兩回,為何還有貪念呢?不,他沒有資格與她有再進一步的接觸,所以一定要拒絕她。
雖然他眼睛上仍蓋著熱敷的小毛巾,但那冷死人不償命的口吻及毫不客套的拒絕字眼,讓範靖喜一時之間有些尷尬不自在。她只能慶幸他暫時是看不見她的,也明白為何助理會突然出這麼大一個槌了。
等等回頭要去好好安慰一下那位小助理,想必現在的她應該很受傷沮喪才是。
光只是聲嗓就可以這般凍人,不難想像當他睜眼時,那凍傷人的指數可以瞬間飆升到何種驚人的境界。
事實證明她的想法是對的,那一回當她為他洗好頭,拿掉他眼上的小毛巾時,那雙冷冽沁透人心的眼眸讓她忍不住打了個寒顫,讓人無法再開口多說些什麼。
「妳叫什麼名字?」臨走前他問。該死的,為何要明知故問?
「您可以叫我小範。」
「嗯!」
從那天之後,每兩個星期他便會出現在「A Game」,出現在範靖喜的眼前。
然而,她不僅接受了他的預約,更是打破一般工作的原則,接下助理洗頭的工作,全程由她獨自為他服務──原因其實很簡單,因為除了她以外,她不認為還有哪個助理或設計師承受得了他周身所散發出的冷空氣,她抵抗力好,不怕凍傷感冒的。
★★★
一如以往,在殷侑丞躺下後,範靖喜便為他敷上放鬆眼睛的熱毛巾,接著便開始為他洗頭兼按摩頭皮。
打從升為設計師後,他是她唯一由洗頭開始全程服務的對象,但即便她早已是個知名美髮設計師,這些工作做起來仍是一點都不馬虎,甚至做得比以往當助理時還要認真仔細。
不是她執意想留住這個客人,說穿了,以她的收入,多一個或少一個客人對她完全沒有影響,相對地,她可以不必讓自己忙碌疲憊;但她就是有個直覺,覺得他喜歡她的服務。
雖然他總是面無表情,也總是能不吭聲便不吭聲,她無法直接從他的反應上得知他是否喜歡她的手藝,但山不轉路轉,他嘴裡不說,那麼就要他的身體說明吧!
每每在為他洗頭按摩頭皮時,感受到他放鬆的感覺並不明顯,但當回到座位上,她拿出精油為他按摩肩頸時,他放鬆的模樣就十分明顯了。
她可以清楚感受到他緊繃的肩頭變得較為柔軟,從鏡面反射出的神情也是,剛硬的線條全在那瞬間變得柔和許多,冰冷感也減去大半。
她知道,他一直是喜歡她的服務的,這一點可以教她很放心地繼續為他在頂上做文章。
當然,在她認真地為他整理頭髮的同時,有時她會感受到他的目光,但當她將視線調向鏡面時,她看見的只有一直將眸光放在落地窗外看著風景的他。
是錯覺嗎?她老是這麼問著自己。
她知道他不喜歡前額的頭髮擋到視線,也不喜歡標新立異過分新潮的髮型,只要看來順暢整潔便可以,所以她一如往常簡單修剪了下他的頭髮,仍是給他清爽好整理的髮型。
沒有特殊狀況,沒有多餘的對話,一切再次順利結束。
殷侑丞離開髮廊後,範靖喜也隨即離開了「A Game」,這陣子她除了先前固定時間預定的客戶之外,其他的時間她並未再接任何預約的客戶,事實上,接下來兩個星期的時間她都不會再接任何預約,因為她要先忙「房事」。
★★★
這間屋子殷侑丞住了兩年,左鄰右舍依舊沒認識半個人,有些鄰居知道他姓殷,還是看他信箱上的掛號單才知道的,但鄰居是誰呢?他一點都不在意。
住在對門的是一對中年夫妻,出入時他見過幾回,他們曾試著對他友好,而他仍總是點頭或搖頭回應,久而久之人家也不再自討沒趣了。
從「A Game」離開後,他便直接驅車回家去,完全沒有在外逛街吃飯逗留的意願。
當他從電梯裡走出來時,眼前擺滿了打包好的雜物,很明顯地,有住戶正在搬家當中。但這層樓只有他與對戶,那表示對戶要搬走了。
正在整理物品的陳太太發現殷侑丞從電梯裡走出,又見他盯著一地打包好的行李直看,忍不住開口說:「不好意思,我們正要搬走,這兩天可能會有些吵雜凌亂,請殷先生多包涵,這些東西待會兒就會搬走了,不會擋路太久的。」
這個對門鄰居安靜得教人難以適從,但她就要搬走了,他除了不愛與人說話之外,也算得上是個好鄰居,從不為社區帶來麻煩。雖然知道其實搬走就搬走,毋需向他特別說明,不過也就剩這一回,再也沒下次了,能當鄰居自是有緣,她也不需要臨走還帶給彼此壞印象。
本以為他該是點點頭就走進屋裡去的,但這回出乎了陳太太的意料之外,他開口了。
「辛苦了,慢慢來沒關係。」
雖然殷侑丞並未客套到說出要幫忙之類的話來,但他那客氣有禮、帶著些許溫度的嗓音,全是陳太太意料之外的反應,這已經夠教她吃驚了。
「好……」看著對面大門開了又關,陳太太真是心情複雜到了極點。
他真心的要她慢慢來沒關係嗎?還是……他早就期待他們搬走已久了?
唉……沒有答案,陳太太只好在心底嘆了口氣,繼續整理一切。而她所不知道的是,當大門隔絕了與所有人之間的接觸時,殷侑丞臉上那股冷絕的神態也在瞬間卸下,換上的是一雙附有溫度的瞳眸。
他不是個天生無情的人,但他必須要自己無情,可能的話,要盡量地與所有人之間情感疏離,包括家人。
不對任何人付出感情,也不讓任何人有機會對他付出感情,這是他對彼此最仁慈、也最不傷人的方式。
坐進沙發裡,他伸手摸了摸自己的頭髮,那輕柔的動作並不是怕弄疼了他自己,而是因為這是她親手為他打理的。
等了又等,究竟等了多少年了,他自己也沒再細算,因為已經沒有那個必要了,他再也沒有那個資格去要回他失去的一切……
這到底算什麼?上天為何要這麼玩弄他呢?他做錯了什麼?每天每天他都問著自己相同的問題不下百回,但百年過了,誰也不曾給過他答案,神仙也好、鬼魅也罷……
究竟還要再幾個百年,他才能終止這折磨人的一切?
思緒陷入了無限的輪迴之中,殷侑丞緊握著雙拳,他恨著,可悲的是,該恨誰他都不知道。
就這樣,他化身為一尊憤恨的雕像,一動也不動地持著相同的姿勢坐在原位上。
當晝光交棒給黑夜,屋外的燈火比屋內亮上許多,殷侑丞仍是不曾移動,直到寂靜的氛圍教刺耳的鈴響劃破,才將他從痛苦的深淵拉回現實當中。
門鈴聲響起,但也僅只一回,像是有些明白,卻又不真明白,所以按下門鈴的手指沒再繼續接連地按著。
隔著大門,站在外頭及坐在裡面的人都安靜地等待著,一個期待著大門開啟,另一個等待平靜返回他的身邊。
約莫過了五分鐘的時間,門鈴聲響並未再響起,這回響起的是屋內的電話。
但電話聲只響了五回便自動轉入答錄機,而他並未在答錄機上留下任何訊息,徒留窒人的空間給想留言的人留言,不想留言就結束通訊吧!
然而,答錄機傳出了那陌生、卻又不真的陌生的婦人聲嗓。
「侑丞……最近很忙嗎?在忙些什麼呢?媽媽來找過你幾回,你都不在家,有空的話回家吃個飯吧!你爸最近唸你唸得緊,要不……打個電話回家也好。」
最後那句話,帶著深深的無奈及嘆息。
留言結束,屋外也回復全然的寂靜,殷侑丞知道她離去了。
她是個好人,但她只是「殷侑丞」的母親,不是他的。
所以……親情間的關愛他不能接受,那只是傷人的無形利器。
這些年,他給予自己與他人的傷害已經夠多了,毋需再增添這一樁了,反正……「殷侑丞」很快便會死去,不是嗎?
「還剩多少時間呢?一年嗎?」他低聲自喃著。
★★★
範靖喜深覺自己十分幸運,她的老客戶陳太太與先生要移民到加拿大與兒媳們同住,在最後一回來給她整理頭髮時提及房子的問題,正好她也想換個居家環境,於是主動開口詢問陳太太可否讓她看房子。
陳太太爽快地答應了她的請求,並與她相約隔日便帶她去看房子。
房子離市區只要十五分鐘的車程,七年屋齡、戶數少,社區環境清靜優雅,社區後側就在山腳下,毋需擔心有任何建商突然在後頭蓋起房子;前側雖是大馬路,但陳太太的房子位於十二樓,又有隔音性好的氣密窗阻隔外頭所有的吵雜聲響,完全沒有猶豫的她,當下就請陳太太將房子賣給她。
她幸運地以一個十分合理的價錢買到了理想中的住宅,所以最近她減少個人工作量,專心地找來室內設計師重新為房子內部做裝潢,自己則忙著清理個人物品,好在裝潢完成後便可在第一時間喬遷入住。
「社區裡的住戶大多房子一蓋好便居住在此,多是家庭單純的人家,妳有任何問題,隨便找個鄰居他們都會很熱心地幫助妳。而住在對面的先生,他不愛說話,但也不是壞人,上回他母親來找他剛好碰上我,我們聊了一下,原來他以前是個刑警,但有一回出了意外傷到了頭部,聽她母親說他昏迷了三天才醒來。本以為幸運地撿回了一條命,但事後才發現他似乎遺忘了部分記憶,甚至算是開朗的個性也完全大變,變得沉默寡言,甚至是孤僻,連自己父母親都不愛來往……」
從新家大門走出來,範靖喜不自覺地望了對門一眼,想起了房子過戶那天陳太太告訴她的話。
搬進來一個星期了,她從沒看過對門的人,也不曾聽過對面傳出任何聲響,若不是陳太太告訴她對門的人已經住了兩年多的時間,當下她真有感覺那是間空屋。
沉默孤僻……想起陳太太的形容,她腦海中立即浮現一個高大的身影。
殷侑丞,這是他在髮廊結帳時簽下的姓名,但其餘的資料他一項也不留,所以除了名字之外,範靖喜壓根不知道他住在哪;而尚未碰過面的鄰居先生讓她想起了他。
「世上會有這麼湊巧的事嗎?」驚覺自己把腦海裡浮現的問號吐出了口,範靖喜失笑地搖著頭,將這荒謬的可能性搖出腦袋外,這才搭著電梯下樓去。
她走到離社區約百尺距離的便利商店裡買了瓶鮮乳,結帳時眼角閃過一抹高大的身影,但她沒有留神細看那抹身影,而是結完帳後便直接走出店家大門離去。
時間接近凌晨一點,路上行人少之又少,連馬路上行經路過的車輛都少,一路上顯得十分清冷,範靖喜下意識地加快腳步。
約莫走了五十公尺,遠遠的就見兩名步伐不太穩的男人與她反向走來,她小心地盡量靠向車道旁走著,那裡的路燈至少較為明亮些。
但她再小心翼翼也沒有用,兩個看來明顯喝了酒的男人見她迎面走來,便吹起口哨,並惡意地阻去她的去路。
「借過。」範靖喜冷冷地開口,並未閃避男人們邪淫下流的視線。
即使心底仍是存著些許恐懼感,但她不能閃躲對方的目光,她必須看著,若他們有任何不軌的舉動出現,才好在第一時間反應。
「好啊,小姐要過,怎麼能不給過呢?」身形較為矮小的男人笑嘻嘻地說著,也依言退了開來。
範靖喜向左跨了一步,正打算繞過眼前的兩人時,另一名身形較為高大的男人卻快她一步地擋住她的去路。
範靖喜只能慶幸自己腳步煞車煞得快,沒有筆直地撞上那名擋路的男人,要不真被吃了豆腐,對方肯定會油嘴滑舌地說是她自己送上門的。
她急急地退了一大步,但也在同時聞到對方身上濃濃的酒味。
「小姐長得好美啊!怎麼自己一個人在路上走呢?很寂寞厚?」原是讓路的男人笑嘻嘻地說,這回望著範靖喜的目光加倍猥瑣,滿滿的慾望寫在眼底。
來者不善,還是兩個滿身酒臭的醉鬼,範靖喜將雙手放在身後,從零錢包裡拿出小型的呼叫器,若兩人真的打算繼續騷擾她,那麼她也不客氣了。
她試著移動腳步向另一頭離去,但仍是被阻去腳步,當下她好後悔自己貪圖方便沒帶手機出門,要不直接報警叫警員來處理就好了。
「小姐不用寂寞,我們兩兄弟今晚就陪陪妳好了,家住哪裡啊?還是肚子餓了?我們一起去吃消夜好了。」男子說完便上前走向範靖喜,並試著朝她伸手,企圖拉起她的手。
範靖喜快速閃過,但另一人直接來到她身後,這下子她真是進退不得了。
「哎呀,這是急著去哪裡呢?我們兄弟在這兒陪妳還不夠嗎?」前頭那名較為矮小的男子說著,而範靖喜身後的男子看見了她手上的錢包及呼叫器,在她不及反應的情況下一把將它搶了過去。
「我知道妳餓了,哥哥我『下麵』給妳吃,包妳吃到撐、吃到吐。」男子話一說完便開始下流地大笑著,連後頭一直沒開口說話的另一人也跟著大笑。
手裡的東西被奪走,儘管心底十分慌張,但範靖喜仍是一語不發,力持著表面上沉著的冷靜,絕不讓對方看見她心裡的害怕。
「哎喲,漂亮小姐怎麼都不笑呢?」說著,站在範靖喜身前的男子伸手就往她臉上摸去。
範靖喜快快閃避,但閃得了眼前的男人,卻躲不過身後的男人。
身後的男人一把拽著她的手臂,一個使勁便打算強行拖著她走。
她用力地掙扎著,下一秒,男人鬆開了手,但並不是她的掙扎有了成效。
「操你媽的!」
她聽見她身前的男人爆著粗口,並轉移了目標不再針對她,接著是肉體碰撞的聲響。
一個高大的身影不斷地送上鐵拳,讓原本拽著她的男人瞬間倒地,而另一名男人見兄弟被揍,自然是氣急敗壞地叫罵著並打算討回尊嚴。
見狀,範靖喜急忙地退到人行道的一旁。她四處張望著,冀望此時此刻能有個路人經過,她才好呼救,因為現在可是一對二,勝算低微啊!
粗俗的謾罵聲響不斷自兩個男人口裡發出,但拳頭打在身體上的聲響也不曾停止過。
現在的情況十分混亂,範靖喜心底的恐懼感要比方才更甚,再也維持不了臉上冷靜的假象。
有人來為她解圍,她固然開心,但若那人受了傷,她更是過意不去了。
張望的結果十分令她失望,因為他們正好處在人行道的中央,一旁的住宅店面全都拉下了鐵門,要在短時間內找人幫忙看來是渺茫了。
心底做了最壞的打算,大不了受點皮肉傷。
範靖喜將視線調回三個纏在一塊的男人身上,這才發現搭救她的不是別人,竟是她的客戶殷侑丞。
只見他不斷地將拳頭落在較為高大的男子身上,而較為矮小的男人則乘機攻擊他,但他似乎感受不到疼痛,直直落的拳頭直到男子倒地了,這才回身還擊另一人。
拳頭落下的聲響,伴隨著的是一聲又一聲的淒慘哀號,很快地,另一名猥瑣男子也倒地不起了,但殷侑丞攻擊的動作卻沒有就此收手停止。
毫不留情的拳頭仍是不斷地在男人身上招呼著,而從地上傳來的淒慘叫喊聲也開始顯得微弱,最後只剩下些微的悶響。
那一臉怒不可遏、像是失去理智的男人,真的是殷侑丞嗎?那個冰冷、一臉無情無緒的男人上哪去了?
範靖喜從怔愣中回了神,無法否認自己被眼前似乎發狂的男人給嚇著了。
他該收手了!
雖然兩名男子騷擾了她,也許是酒精作祟的關係,也或許他們本身就不是什麼好東西,一切都只能說是他們活該,但她終究是安全無恙,而他……也該停手了才是。
★★★
殷侑丞知道對面搬來了新的住戶,本是不在意的他卻在不經意的時刻,看見了不容錯認的身影,心底兩股不同的情緒狂烈地拉扯著他的情感及理智。
他希望是他看錯人了,卻也知道自己不可能認錯她的身影;他希望她只是路過這個地帶,卻也知道她不可能沒事來到這裡;他希望她的目的地不是他所住的社區,卻又親眼見她走了進去,身旁陪著她的不是別人,而是他對門的鄰居太太。
如果可以,他只希望她剛好與鄰居太太是朋友;如果可以,他只希望她別住進那間屋裡;如果可以,他只希望她能夠離他遠遠的……
這些日子他努力地不出現在她眼前,他甚至打算取消下回去「A Game」的預約,或者……對自己再狠心點,連往後的預約都一併取消,不再給自己每個月見到她的機會,即便想看著她,也只躲在她看不見的角落裡就好。
只要看著就好,他什麼都不說、不做,他會努力辦到的……不,是一定會辦到的。
所以最後,他只能選擇最消極的逃避,避開所有能與她正面相遇的機會,就連方才在便利商店裡,他也是全然地背對著她。
只要他願意,他可以當個咫尺陌生人,這不難的,再難……也只要撐過一年便足夠了,或許壓根只要幾個月的時間。
他打算在這個身體閉眼之後,當他再度睜眼時,他要當個遠遠看著她幸福的陌生人,不再放縱自己的渴求去接近她,再也不了……
可是當他發現想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情,真要確切的達成,卻是困難重重。
當他看見兩個混蛋正在騷擾她的那一刻,他的理智全無,腦子裡唯一的念頭是殺了那兩個垃圾。
殺了他們、殺了他們、殺了他們……每落下一拳,相同的字句便在他心底默唸一回,怎麼也停不下來。
他不知等了多久,才找到了心心念念的她,他們怎麼可以這麼對待他的心頭肉?憑什麼、憑什麼……
不知不覺中,他落拳的力道一回比一回更重,指節破了皮更是毫不自覺,連耳邊那些淒厲的哀號聲何時消失都不知道,他只知道他停不下來。
「別打了、別打了……」範靖喜在一旁大聲喊叫著。
躺在地上的兩人別說是還擊了,現在他們就連哀叫的力氣都沒有了,再這麼下去真要去見閻王了。
但不論她如何喊叫著,殷侑丞狠厲的動作卻是不曾停頓,拳頭仍是一次次地落下。
情急之下,顧不得自己是否會受到波及而受傷,範靖喜猛地向前從他身側撲抱著他,阻止他繼續揮拳。
「夠了、夠了……」範靖喜其實有些害怕他會失去理智地連她一併都打,但她仍是鼓起勇氣地使勁推著他,打算將他推到人行道的最內側。
只不過,當她推了又推,不論如何使勁都無法移動他半分,心有些急了,於是抱著他的雙手跟著不斷地縮緊。
所幸,雖然無法讓他遠離地上的兩人,但至少他停下了手,那兩個人不用死了,他更不用擔下殺人這項罪名了。
事實上,殷侑丞不想停手的,當不當個殺人凶手,對他而言不重要,更是沒有意義,他不在乎。
他在乎的是,懷裡緊緊抱著他的人兒……
這是兩人分別後第一回這麼親密地碰觸,那氣息、那溫度,都是他闊別以久的想念滋味,只差了那麼一點,他幾乎要忘情地喊著她的名,幾乎……
範靖喜咬著唇,緊抱著殷侑丞的雙手依舊沒有鬆開,只是她閉著雙眼,不敢去面對可能會挨揍的情景。
每每閉起雙眼的當下,不論是回憶,亦或是夢境之中,她一直在他懷中不曾離去過,而他更是不曾鬆手過。
於是,他下意識地舉起手想環抱著她,但下一刻,舉到半空的手僵住了。
他這是在做什麼?她雖然是小喜,但已經不是當時屬於他的小喜了。雖然只要他願意,她可以再是他的小喜,但他不能自私地這麼做……
範靖喜以為打紅了眼的男人可能會連她都揍,但等了又等,她沒等到預期中的疼痛,耳裡卻傳來他的聲音。
「小鐘,這裡是……馬上叫人過來處理。」
原來他拿出手機打電話,但由於尚未從混亂的一切中恢復驚惶的心緒,他究竟對著手機另一頭說了些什麼,她聽得不真切,只知道在他結束通話的那一個瞬間,她緊緊抱在他腰際上的雙手被扒了開來。
「嗯?」她以為他就要推開她,但預想卻出錯了。
殷侑丞是扒開了她緊束著他的雙手沒錯,但並不是為了推開她,而是為了帶她離開這髒亂混亂的現場。
他一手握著她的手肘,彎腰拾起她的零錢包及呼叫器後,這才不輕不重地拉著她快步往所住的社區方向前進。
在被動地跟著他行走的當下,範靖喜腦子裡一片空白,無法思考。
直到他拉著她走入電梯裡,在密閉的小空間裡,不知是否是她的錯覺,空氣流動似乎有些稀薄窒人,但這讓她空白的腦袋恢復了思考空間。
剛才他的通話內容,她隱約有些印象,現在狀況很明確了,那兩個騷擾不成卻被打得倒地不起的男人會被送進醫院及警局,但她確定是不必跟著去了,因為他在電話中都為她打點好一切,省去不少時間與討人厭的煩事。
但重點來了,他為何帶著她搭上電梯,還準確無誤地按下了十二樓的按鍵?為何他會知道她住哪?為何他手上有住戶的安全磁扣?會不會真的那麼湊巧,他也是這裡的住戶?
想著並不會有答案,不如開口問了。
「你……是這裡的住戶嗎?」範靖喜小聲地問著,這時殷侑丞也鬆開了她的手,不再握著她的手肘,並把她的錢包及呼叫器還給她。
其實她想問的是他是否就是她對門的鄰居,因為這個社區的安全磁扣每棟大樓都不同,甚至每層樓的也不同,那表示一個磁扣就只能去一個定點樓層,簡單的說,十二樓只有她與對戶的人才能毫無阻礙地上樓。
我是,而且就住在妳的對門。
話問出口了,但殷侑丞並未開口回應,只是側過臉看了她一眼,便又專心看著電梯樓層跳動的數字。
他臉上仍是掛著一副冷漠的模樣,似乎剛才什麼事也不曾發生,而他不過是剛好與她搭上同一部電梯,如此而已。
但範靖喜可無法保持冷靜的心緒,因為方才在路上,燈光沒有電梯裡明亮,現在她才看清他臉上的「顏色」。
「你受傷了!」她的語氣裡有著掩不住的擔憂,但不意外地,男人再一次忽視剛才的話語。
右邊顴骨上印著一記青的,左唇角上一抹紅的,沒有猶豫地,她伸手拉起他的大手一看,沒意外地看見他破了皮的指節。雖然跟躺在地上的那兩人比起來,他這些傷不算什麼,她甚至很意外他一個能打倒兩個,但他的傷可是為她而來的,這些是她看得見的地方,那麼衣服底下那些看不見的又有多少呢?
思及此,範靖喜眉頭皺得緊,若不是顧及兩人關係不夠熟稔,她會一把拉起他的上衣,看看他身上究竟還有沒有其他傷痕存在。
她思索著該如何開口說服他脫去上衣讓她檢視,但還沒能想出個好說詞,電梯門滑了開來,十二樓到了。
殷侑丞無聲無息地抽回自己的手,並率先跨出電梯之外。
看著自己空盪盪的手心,範靖喜吶吶地跟著走出電梯。
她沒看著自家大門,而是將視線停駐在殷侑丞身上,看著他拿出鑰匙打開大門,這才證實了她的猜測。
他真的是她對門鄰居呢!
這意外的巧合讓她感到十分神奇,但緊接著的關門聲響,讓她愣住了。
就這樣?連聲晚安再見都沒有?望著緊閉的大門,範靖喜心情十分複雜。
些許的尷尬、些許的憤怒綜合成為莫名的不知所以,她以為至少他會道一句再見什麼之類的話語,但什麼都沒有。
今天的他顯得十分無禮,以往在店裡,他要離去時至少還會看她一眼,但今天他連那一眼都沒給,是怎麼樣?氣她害他挨了好幾拳嗎?
範靖喜帶著氣憤的心情拿出鑰匙,進屋後便用力地關上大門。砰地一聲,偌大的聲響在樓梯間響起,她可以肯定這聲響鐵定傳進對門裡了。
揚起嘴角,但笑意壓根沒有浮起,那種得意的快感更是不存在,有的只是莫名的空虛及雜亂的思緒。
為了甩去那些負面的感覺,她決定好好睡一覺,明天醒來就把今晚的一切給忘個精光。
睡覺、睡覺、睡覺……
躺在柔軟的床舖上,範靖喜在心底不斷地重複要自己睡覺,通常這麼對自己喊話,她都能很快入睡,而她也相信今晚不會例外。
★★★
她這是在幹什麼?
範靖喜瞪著自己按下門鈴的右手,再瞪著自己拿著醫藥箱的左手,她覺得自己真的失常了。她早該入眠作美夢去了不是嗎?怎麼今天居然睡不著,不論左翻還是右滾,睡不著就是睡不著……
但現在轉身回到屋裡似乎也來不及了,尤其是她不止按下一回門鈴,而是該死地連按了兩回。半夜三點鐘,連按了別人家的門鈴兩回,她能奢想他早已深深入眠,完全沒聽見門鈴聲響嗎?
好吧,按了門鈴卻急忙逃走,像個惡作劇的孩童,是十分無禮的行為,那就再等一分鐘吧!若一分鐘後屋內沒有任何回應,那麼她就轉身走人。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
她開始無聲地數著,當數到六十的那一刻,她會毫不猶豫地轉身回家去。
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只剩最後三秒鐘了,再三秒她就能回家睡覺去了。
範靖喜向後退了一小步,正打算要轉身走人,耳裡卻傳來了聲響,接著眼前原是緊閉的大門居然開啟了。
她瞪著前方,當殷侑丞的臉進入了她的視線範圍內,她便瞪著他。
「妳……」殷侑丞雖是面無表情,但當他打開大門的那一瞬間,發現門外站的不是別人,而是他日日夜夜無法不去想念的身影時,他黑黝眸底閃過一抹驚訝,想逃的念頭更是在他腦海裡浮現。
半夜三點鐘聽見門鈴聲響,他第一個反應是不想理會,但最終仍是敵不過好奇心的驅使來應門;雖不知道門外究竟會是誰大半夜地來按鈴,但他從沒預想過會是她。
但最終,他什麼也沒做,就只是面無表情地看著她,毋需開口提問,因為她手裡的醫藥箱已經為她說明了來意。
原本一聽見開門的聲響,範靖喜忍不住在心底大罵自己的無禮舉動,半夜三點鐘,一個正常人是不會隨意去按別人家的門鈴的,將人從睡夢中吵醒不僅不禮貌,甚至可能還得承受對方的怒意。
若他生氣了,她可以理解的,但當那張仍是冷然的臉入了眼,她心底那股複雜的情緒又再次被撩起。
算了,管他是不是從被窩裡爬出來開門的,他先前那冷冷的態度想來就教人生氣,雖然不知為何,但那時她就是明顯地感受到了他無聲的怒氣。
怎麼,她做錯了什麼?她也是個莫名的受害者,還是他氣她阻止他將人打死?他就這麼想當殺人犯嗎?
越想越氣,她不再自責自己無禮的行徑,反而有些理所當然地挺起背脊說:「我來幫你擦藥。」
她開口說了話,他不回應,已經不讓她意外了,她知道一定要習慣他這個不愛說話的壞習慣,只是她沒想到一個人無禮的態度可以發揮得這麼淋漓盡致,教好脾氣的她都忍不住想破口大罵了。
是的,殷侑丞什麼話也沒說,望著她的眼眸冷得幾乎是要冰凍一般,而這些都不是教她氣憤的,是他打算關起大門的動作惹火了她。
只不過他的動作不快,更沒想到她居然會大膽地伸手阻止他關門的舉動。
就這樣,殷侑丞面無表情地望著範靖喜,而她則是生氣地繼續瞪著他。
「我不需要上藥。」他終究是開口拒絕了,因為他不得不。
拉著門把的大手不敢用力拉上大門,就怕傷了她,而這正好給了她機會。
「我只是想幫你上藥,不管你要還是不是,至少我不想讓我自己良心不安,更不想讓自己對你有所虧欠。」範靖喜用力將大門扳開,不經思考便將心底的話直截了當地說出,一臉的堅持,訴說了不達目的不肯罷休的決心。
望著那張固執堅決的小臉,殷侑丞有種時光倒流的錯覺,彷彿她從不曾自他身邊離去過。
小喜……一幕幕不曾自腦海消去的回憶突地快速湧上,幾乎將他淹沒,而耳裡再度傳來那熟悉不過的細膩聲嗓。
「給你兩個選擇,一個是讓我進屋去,另一個是你跟我進屋去。」前一句指的是進他的屋裡,後面那一句則是進她屋裡,她知道他懂她的意思。
二選一,沒有要不要。
── 百年孤寂 永世追尋 ──
最熾熱的情意 只能用冷漠包裝
果麗《幸福給不給》 11/4都怪月老愛凸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