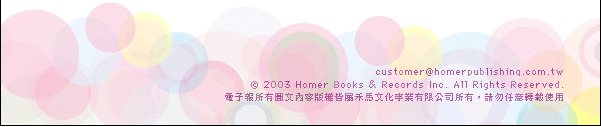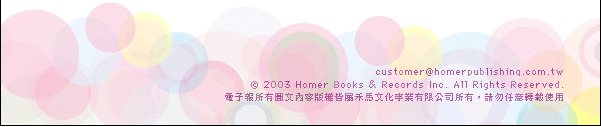那天的月色裹了一層霧。
如果不是夜色太朦朧,如果不是因為好朋友金克勤臨時有事沒辦法到「上弦月」俱樂部打工的話,她也不會自告奮勇去代班;如果不是因為自告奮勇替金克勤到「上弦月」去代班當泊車小弟,她也不可能會遇見那個上門來尋歡買醉的男人,更不可能被他誤認為是個「小子」,當然也就不會有這個故事的發生了。
故事第一章就發生在那個彷彿裹了一層迷霧的夜色裡。
夜色中,上弦月俱樂部燙金的大門開了,先是一陣輕微的口哨聲響起來,接著吹口哨的男人在門內出現,她看見他大手揮開上弦月裡最受歡迎的紅牌女郎,邁開步履搖晃的酒醉步伐走出來。
如果是金克勤在這裡的話,一定會趕忙上前去扶客人一把,既然她是代替好友到這裡來打工,當然也應該這樣做。想也沒想,她就趕上前去,想不到對方寧願醉得東倒西歪也不肯接受幫助。
「我沒醉!」大手朝空中一揮,踉蹌幾步,男人裹著上等質料褲子的屁股宛若皮球著地後接連幾個反彈,咚個隆地咚,一個階梯、兩個階梯、三個階梯,就這樣,他成了上弦月俱樂部開店營業三十年以來,第一個不用雙腳而是用屁股下樓的酒客。
「月色很美,對不對,小子?」皮球酒客滾坐在台階底下,眼睛看著她,用口哨聲來掩飾尷尬。
她想了一秒,才意識到他所謂的「小子」指的就是她。
「很冷!」一抹烏雲飄過來遮住月亮,「月亮躲在雲霧後面根本看不清楚!」她抬頭看看天空,務實的開口。
「我說夜色很美你跟著說很美就是了,別唱反調。」男人停止了吹口哨,「小子,我的脾氣不太好。」
「你生氣的時候會怎樣?在地上表演驢打滾?」她不慍不火地問。
男人揚起眉頭,烏雲閃過月亮露出來短暫照亮他的臉,一頭及肩長髮梳成馬尾紮在腦後,鮮明的五官輪廓透露出輕狂任性。他很年輕,最多不會超過三十歲,年紀輕輕的有錢大少不可能受得了來自一個泊車小弟的羞辱,想到這裡,她感到幾分後悔,畢竟她是替金克勤來代班的,如果因此害人家丟了飯碗就糟糕了!
幸好等了三秒鐘,自稱脾氣不太好的男人並沒有勃然大怒。
「瘦不拉嘰的娘娘腔!」他只是揚著眉頭說,「看不出你很帶種嘛!」醉眼裡反而流露出一抹讚賞意味,「說說看你身上這套衣服是哪裡弄來的?」
「特別在西裝店訂製的。」她簡短地說明,但省略了西裝師傅是按照金克勤的身材訂製的;金克勤是學校籃球隊的隊長,長得又高又壯,他的西裝穿在她身上就像套了一個大布袋套,那男人顯然也心有同感。
「那個西裝師傅真應該改行去做布袋!」他哈哈一笑,明顯認為那套白西裝太大了,更顯出穿它的人愈發顯得弱不禁風。
「布袋通常是用來裝米的。」她說。
「不只是裝米,不只是裝米……」男人被酒精侵蝕的腦細胞轉了轉,「也許還可以用來裝屍體!」咧開嘴,他亮出一口白牙。
口氣彷彿出自預謀殺人犯的恫喝,但她不為所動地開口:「先生,我不是被人嚇大的。」
「我曉得!」男人嘴咧得更開,「你是還沒有變過聲的娘娘腔。」
「我二十一歲了。」她驕傲的宣稱。
「失敬失敬,原來是變過聲的娘娘腔。」他立刻改口。
她氣得七竅生煙,卻又憋著一肚子氣不敢發作。
「好啦!我想你是天不地不怕的!」他露出得逞的醉笑,瞅著她,幾秒之後又想起了什麼煩心事地皺起眉頭,「去吧!」他從西裝口袋裡摸出一把鑰匙胡亂扔出去。
就一個醉客來說,他的準頭算不錯了,至少沒有丟到西天外去。她急忙後退兩步又快步往左前方追了幾步,在鑰匙落地之前總算接住了。
「把我的車開過來。」大少爺接著發號施令。
「請問你的車……」
「停車場裡最貴的那輛就是!」
他不耐煩地手一揮。
★★★
就是就是!
什麼跟什麼,有錢了不起啊!
她咕噥著從停車場把最貴的一輛車開過來,發現那狂妄之徒竟然還沒辦法從跌坐在地上的困境中解脫出來。
看來他是醉得剩下只能控制一張壞嘴哩!
但她可不想再去招惹他,只是打開車門站在門邊,宛如車掌小姐等候乘客自己爬上車來,好來個關門送客,沒想到她那樣站著也不行,也惹惱了他。
「你那是什麼眼神?」男人的眼神在冒火。
「我沒什麼意思。」她一雙無辜的大眼睛眨了兩下。
「你覺得我開不起那輛車是吧?」火上好像又澆了油,他也不知道自己幹嘛對個泊車小弟發這麼大脾氣,也許是對方那雙太像女孩子的眼睛讓他有種奇怪的錯覺,弄得他竟然心浮氣躁了起來。
「你配這輛頂級名車確實是相得益彰。」垂著頭,她一副必恭必敬的樣子。
算這泊車的識貨!純手工打造的世界級名車,停車場裡最貴的一輛,全球限量,全台灣唯一一輛經典款。
「所以你也覺得我身上散發著貴族氣息?」他仰起驕傲的眉眼瞅著她。
「當然!」她繼續恭恭敬敬地開口,「綁馬尾巴的假惺惺男人,跟這輛假惺惺的歐洲貴族名車配得剛剛好。」
「你這臭泊車的娘娘腔……」
「你站起來了!」她張大嘴巴打斷他的辱罵。後退兩步,奇蹟似的瞪著他站得直挺挺的雙腿,彷彿那是剛學會走路的孩子,超過一百八十公分的超級大孩子。
超級大孩子眼眸往下一垂,「咳……」他動手拍掉屁股上的灰塵,「你故意激我站起來的?」一副不知該責備還是感謝她的尷尬表情。
「只是激而已,」從頭到尾她可沒有妄想圖謀什麼感謝,「但沒想到你會突然像被踩中尾巴的貓一樣跳起來。」
「被踩中尾巴的貓?」他的眉頭攢了起來。
「你覺得『鯉魚躍龍門』好聽一點也行。但不管是飛起來的魚還是跳起來的貓,我一點都沒有想幫你脫困的意思。」她說。
「意思是你比較欣賞我跌在地上的樣子?」醉酒的腦袋頓時清醒了一大半,眼珠裡的血絲也消失了不少,就連壞脾氣也連帶收斂了幾分,大個子唇邊甚至掀起一抹笑意。
「我欣賞的是在哪裡跌倒就在哪裡站起來。」她說。
「說得好!」男人懶洋洋地鼓掌,「你當泊車的太可惜了。」他的眉頭抖了一下。
「泊車不偷不搶並不可恥。」
這話夠讓他酒醒了百分之兩百啦!一個滿口大道理的泊車小弟。
「你新來的?」他的眼眸裡多了幾分興趣。
「我是來代班的。」
「原來是代班的。」他從腳到頭打量她幾眼,「難怪你不認識我。」
「我不認識你,但是在報紙上見過你,你是一把難解的鎖!」她無畏無懼地喊出他的大名:「雷步森先生。」
雷步森,確實是一種昂貴又難解的鎖。取這名字的正是他那出了名的天才開鎖神匠老爸雷昊群,全球最大鎖類製造商,從開鎖製鎖到跨足房地產,締造出富可敵國的企業體。
「這可巧了,我老爸也這樣說過我,他用雷步森鎖替我命名的時候,並沒有想過我會變得跟那種鎖一樣難搞。」雷步森越過她跨進車內,一條腿卻充滿挑釁意味的懸在車外,存心讓等著關門的菜鳥沒辦法把門關上,除非那娘娘腔有膽子夾斷千億富翁的獨子的腿。「怎麼,你想試著解開我嗎,心靈大師?」他挑釁的眸光懶洋洋地抬起來射向她。
「我不是心靈大師!阿彌陀佛,幸好我也不會開鎖!」她眼珠微微往上一翻,「就算我會,也用不著解你這一把。」她再翻下來瞪著他的眼,「我只希望你趕快把腳伸進車裡,讓我順利關上門……或是你要我乾脆把門打得更開,好讓你從車子裡滾下來?」她試著不慍不火的問道。
「你敢讓我從車上滾下來可就要倒大楣了,泊車的。」雷步森眉頭一動,「如果你換一種態度的話,也許我會給你很多小費。」
「我來這裡代班不是來這裡賣身的。」她一本正經地回答。
血絲褪去的眼眸改成充氣似的愈瞪愈大,「老天!」雷步森拍了下額頭,笑倒在方向盤上。「哈哈……哈哈,我的天……」笑出眼淚,「有意思!有意思!」伸手抹掉笑出的眼水,手掌朝大腿一拍,「娘娘腔,你叫什麼名字?」他抬起眼,充滿研究意味地盯住眼前巴掌大的小臉。
她往後退兩步,凌亂短髮下的小臉築起防備,「泊車的。」她從過長衣袖中伸出手攏攏白西裝,「你只要這樣叫我就行了。」
「泊車的?」雷步森的左眉隨著疑問句揚起來。
「對!」小臉充滿防禦性地點了點。
「你的家人朋友呢,他們叫你什麼?」雷步森繼續問。
她想了想,反正過了今夜,結束代班打工後,他們不會再有交集。
「我叫舒知微。」她說出自己的名字。
「舒知威?」雷步森確定什麼似的重複道。
她知道他搞錯了,不是威而是微,不是男孩而是女孩,但是對一個酒客解釋這麼多也沒用。反正他只是一個不重要的陌生人,陌生人高興叫她小子或是舒知威都悉聽尊便,她才懶得糾正他。
「舒知威小子,你剛剛說你二十一歲了,應該還是大學生吧?」雷步森卻對她流露出高度的興趣。
「大學三年級。」她被動地點點頭。
「我猜你念的是師範大學,以後要當老師的那種人。」半秒之後,雷步森又說。
「你怎麼會知道?」這下舒知微不得不吃驚的張大了嘴。
她確實念的是師範大學,教育系三年級,從小她的志願就是當老師。
「簡單得很,你長了一張愛說教的臉。」
「如果你以為仗著有幾個臭錢,就可以隨便侮辱別人的話,我告訴你……」
「我沒有侮辱你的意思!」雷步森打斷她,「事實上,我還挺喜歡你的,我是說,你跟我很像。」
「我是乖乖牌,從來沒有人覺得我會跟一個渾球很像。」
她拐著彎罵他是渾球,但被罵是渾球的雷步森卻不以為忤地咧開嘴。
「也許因為你自己並不真的了解你。」
「世界上沒有誰能真正了解誰。」
「至少你讓我有了想試一試的念頭,這很少見!」他強調著,「通常我對誰都沒有耐性,對誰都不超過三句話就說不下去了,但對你不一樣。」
「也許那是因為你老是喝得太醉的關係。」
「我是喝得不少,但從來不曾喝醉。」他清醒地望著她。
「喝醉的人通常不會承認自己醉了。」舒知微說,「但是以你的狀態而言,酒醉上道絕對不會有好下場,或許你該叫個人來接你。」
「我開車技術好得可以一路開上天堂。」雷步森用一種聽起來很欠揍的音調說話,臉上的表情也很欠揍。
「阿彌陀佛!希望別人不至於倒楣得跟你開上同一條路。」但她當然不至於揍他,揍人是要負法律責任的。「至於你,你高興開到天堂或是地獄都隨你高興。」
「我想你不喜歡我,小子。」
「我對你沒有喜歡或不喜歡,對你父親而言你是一道難解的鎖,對我來說,你只是今夜例行工作中有待完成的一個。」舒知微有條不紊地說。
「不愧是未來的老師,果然伶牙俐齒,很會說話!」
雷步森接著做出一個驚人之舉,他打開車裡的一個抽屜,抽出一只牛皮紙袋塞進她懷裡。
「或許這裡面的東西可以讓你變得柔軟一點!」魔術師般神祕的笑容浮上男性略帶譏誚的唇角。
舒知微依言打開牛皮紙袋,探頭一看,她像中槍似的渾身一震。「這是……」靈活的舌頭果然打了好幾個結。
「六百萬小費!」他的口氣聽起來像是談成了一件稱心合意的買賣。
「我做了什麼?」她一臉迷茫。
「你讓我生氣,」他眉頭動了動,「你讓我發笑。不管讓我生氣還是讓我笑,都不是平常的人做得到的。」
「我不懂……」
「你不需要懂!」雷步森用結論式的口氣,「總而言之,比起一般逢迎拍馬的傢伙,你有意思多了。」
「有意思?這話你說了很多次!」喜怒無常的傢伙,她完全被他的不按牌理出牌搞迷糊了。「但我是幫人泊車的,不是被人耍的猴子。」
「你不是猴子,你有自尊,有膽識。」雷步森笑一聲,「還有你很帶種!」頓了半拍,又補了句:「你身上什麼都有,就是少了錢的味道。」懸在車外的那條腿突然一縮,拉起車門一關,咻的駕車開個老遠。
★★★
你身上什麼都有,就是少了錢的味道!
如果他是想用錢侮辱人,大可把鈔票撒到地上再命令她跪著一張一張撿起來,金克勤說他在上弦月親眼見過有錢人那樣玩的。但雷步森不玩這一套,她一再挑戰他的權威,結果卻換來一大筆鈔票!
但一味傻在那裡也不是辦法!
從小她就知道要怎麼收穫就要怎麼栽,袋子裡的千元大鈔,沒有一張是她栽的種的,也沒有一張是該她花的用的。
捧著鈔票一路狂追,追出上弦月的大門口,但那「最貴的一輛車」不是跑的而是用飛的,三兩下就從她的眼睛裡飛走,沒入遙遠的黑夜裡。
舒知微從沒想過這種電影情節會發生在自己身上!
她最討厭沒有結尾的電影,沒想到自己就遇到了一個。那傢伙莫名其妙塞給她一大包千元大鈔,連拜拜都沒說就揚長而去,留下一大堆問號。
唯一的解決之道,就是把那一大包問號丟進機車裡,午夜十二點交班過後,立刻騎到警察局去報案。
她不知道雷步森的豪宅在哪裡,但警察總有辦法把那包鉅款物歸原主。
就這麼辦!
午夜過交班後,她一陣風似的騎上機車朝警察局方向疾馳而去。才剛上路不久,騎過一條大馬路,再轉幾個彎,進入一條巷子,就看到那「最貴的一輛車」停在一盞路燈前面。
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沒想到她連騎到警察局去的路程都省掉了。
二話不說,舒之微立刻騎過去,隔著電線桿,停在那「最貴的一輛車」後頭。安全帽還沒來得及脫下,啪噠好大的甩車門聲,先清楚傳進耳朵裡。她暫時停止脫帽,從電線桿後探出頭去,一名染成瑪麗蓮夢露髮色的性感女郎映入眼簾。
女郎站在「最貴的一輛車」車門外,穿一襲銀色低胸迷你晚禮服,肩上披著質料柔軟的上等皮草,臉上卻掛著忿忿不平的表情。一雙媚眼瞪得大大的,彷彿想用眼神把什麼東西從那最貴的車窗裡逼出來。瞪了半天,眼見車內沒有任何動靜,女郎忍不住彎下腰──
乖乖!那女郎的身材真不是蓋的!豐滿的胸部像兩團呼之欲出的蜜桃,結結實實地擱在車窗上。
「雷步森,」女郎嬌滴滴地朝車內喊道,「你到底要不要回家去把那輛拉風的敞篷車開出來,載人家去山上夜遊嘛?」
「寶貝,」聲音低沉得會讓人起雞皮疙瘩。「我說了今天沒辦法。」
女郎不依地扭扭兩顆擱在車窗上的熟成蜜桃。舒知微嚥了一口口水。沒辦法,那女的看起來實在太誘惑,會想咬上一口是人之常情!
難怪雷步森會忍不住下來咬……不是啦,是下車來安撫她。
他先拉拉金髮女郎的手,「不要啦!」女郎扭掉肩上的皮草,露出奶油色澤的胸口和臂膀,然後就像警察把現行犯壓制在牆上,只是負責扮演現行犯被制住的竟然是雷步森,前凸後翹的俏女警搜身似的在他身上施展摸索的誘惑術,然後兩人半推半就的「以牆為床」,上演了一段活色生香的十八禁。
幸好舒之微二十一歲了,而且既然人家敢演,她沒什麼道理不能停看聽。
「森,你說嘛說嘛!」女郎要求著。
「說媽?」雷步森故意裝胡塗。「妳的媽還是我的媽?」
「不是你媽媽也不是我媽媽,我要你說你說愛我!」
「那個妳知道就好了。」
「人家就是要嘛!」女郎不依地在他身上磨蹭著,「我們都快結婚了,你到現在都沒對我說過那三個字。」
「妳是我的未婚妻,這就代表了一切,那三個字不重要啦,「有些事情說穿了就不美了!」
哎喲喲喲!這雷步森還真能扯。舒知微聽了肚子都疼了,自以為在演文藝片啊,說穿了就不美了?不夠噁心還真說不出口!
相較於她這個噁心想吐的電燈泡,雷步森那身材火辣的未婚妻倒是挺吃那一套,姑且把「我愛妳」什麼的丟到一旁,兩人扭麻花似的又扭攪了一陣之後……
「對了,你剛剛說沒辦法是什麼意思?」女郎咬著雷步森的耳朵氣喘吁吁地又問。
「什麼沒辦法?」雷步森咕咕噥噥的,好像在嫌女人怎麼這麼多問題。
「人家要你回去換開敞篷車上山夜遊的事。」
「我以為妳忘了。」
「我記憶力好得要命。」女郎一派任性。
「寶貝,現在凌晨一點鐘了。」
「所以才要夜遊啊!」
「我說了今天不適合。」
「今天正是時候!」豐滿的女性肉體在男性身上磨蹭了一陣,「就像上次一樣,我們開著敞篷車上山去,山裡有別墅在開派對,我們可以通霄跳舞,一定很好玩。」女郎露出一抹足以融化冰淇淋的熱情笑容。
「可是好像快下雨了,」雷步森聲音低沉地說,「而且我那輛敞篷車也不在了。」
「不在了?」
女郎的耳朵好像突然變長,舒知微的也一樣,像兔子一樣豎得老高。
「我把它賣了!」他聳聳肩,「六百萬!」
六百萬!原來放在機車肚子裡的那筆錢是他賣掉敞篷車換來的,舒知微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
「你用不到那輛車十分之一的價格就把它賣了?」那輛敞篷車至少市價六千萬跑不掉。「為什麼?」熱力足以融化冰淇淋的甜蜜嗓音不見了,女郎的聲音變得有些刺耳。
「如果妳受得了的話,我就告訴妳實話。」
「如果你不說清楚我才會發瘋。」拔高嗓音,女郎尖銳地說。
「我得把敞篷車賣了,否則償還不了上個月積欠的信用卡費。」
空氣陷入一陣岑寂,幾秒過後,女郎茫然若失的問:「這是什麼意思?上個月積欠的信用卡費?」
「意思很簡單,」雷步森很乾脆的開口,「我那有錢的老爸不肯買單了!」
「但你是他唯一的獨子。」女郎頓了一下,補了一句:「也是雷氏企業堂堂的總經理。」
「總經理頭銜對我而言也是過去式了。」
安全帽底下,舒知微一張嘴驚訝得像煮熟的蛤蜊般開開的,女郎的聲音則是開始結冰。
「到底怎麼回事?」女郎從雷步森懷裡掙了出來。
「磨練!」失去懷中的軟玉溫香,雷步森轉而背靠在牆上,從口袋裡摸出一根菸點上,抽了幾口,「我老爸不知道哪根筋不對勁,幾個月前突然把我踢下總經理的位子,要我自己到外面去闖蕩磨練看看。」他吐了個煙圈,「其實我根本不是那塊料,闖不闖蕩磨不磨練都一樣。」
「你確定雷伯伯不是在開玩笑?」女郎小心翼翼地問道。
「他先把我踢出公司,接著再踢出家門,妳說他是認真的還是開玩笑?」雷步森把問題丟了回去。
「踢出家門?」
「別擔心,我租了一層五十坪的公寓,一個月才十五萬,便宜得要命。」
月租十五萬叫便宜得要命,那麼眉頭不皺一下就砸下六百萬小費就不足為奇了。什麼叫不把錢當錢,什麼又叫花錢如流水,舒知微算是眼界大開啦。
「噢!」女郎鬆了一口氣,「我就知道你父親不會放任你不管……」
「但我只夠付掉上個月房租,房東說這個月再不付錢,就要請我搬家。」雷步森深吸最後一口菸,「老爸把我戶頭裡的錢全都轉光了。不賣掉敞篷車,我根本沒辦法付清房租和信用卡費。」
「呃?」女郎的下巴好像快掉下來了。
「想不到吧!」他搖搖頭,「連我自己也想不到……」丟下菸蒂,昂貴的皮鞋踩熄了它。「想不到才有意思,不然這個世界就太無聊了,妳說對不對?」
「如果你肯跟雷伯父好好談談……」
「我跟他談過了,結果就是像妳現在看到的這樣。」他攤攤手。
「但你知道,我不可能……」女郎開始結巴。
「妳不可能跟一個一無所有的傢伙在一起,更不可跟我走進禮堂了?」雷步森替她把話說完。
女郎沒有回答他的問題,接下來卻用行動說明了一切。
她款擺著腰肢走到牆角,拾起滑落的上等皮草披回肩上,「現在我要走了。」她臉上的柔情蕩然無存,一臉絕情地開口。
「真可惜,原本我想把這部車也賣了。」踱到黑亮的車頭蓋前,雷步森反手撐在上面,「手頭上有了一筆錢,可以跟妳過幾天痛痛快快的好日子。」他故作歡快的道:「這輛車值不少錢,比敞篷的值更多,賣了它我照樣供得起妳想要的一切,珠寶、首飾、貂皮大衣,或是到任何妳想去的地方度蜜月。」他像拍拍好馬似的拍拍車頭蓋,再跳上去坐著,一雙長腿晃啊晃的。
「對不起。」女郎開始往前走,路燈將婀娜的女性線條拉得長長的,她用如冰塊的嗓音說:「我突然想起還有個約會,快要遲到了。」繼續沿著巷口往前走,彷彿完全沒聽見他的提議。
彷彿預期中婚禮和蜜月的女主角都不是她,而是另有其人。
舒知微瞠目結舌的目送她,在盡頭向左轉,高跟鞋的叩叩聲迴盪在午夜一點寂靜的空氣裡,也像空氣一樣消失在那個轉彎口。
★★★
好安靜!
彷彿女郎的腳步聲帶走了一切。
世界停止了運轉。
萬籟俱寂!
接著一串奇異的呢喃劃破了凝固的岑寂。
是雷步森在吟唱著一種古老的曲調,呢喃愈來愈低,漸漸聽不到了,雷步森的背影卻漸漸僵硬,彷彿化為一尊鑄在車頭蓋上的雕像,硬硬地、冷冷地,彷彿他就在那裡永遠生根佇立,冷不防地,夜色卻突然伸出一隻無形的手將雕像硬生生地推倒在地,砰地發出一聲巨響。
舒知微趕忙跳下機車跑過去,再一次,看見男人跌坐在馬路上的模樣。
他看起來就像一個被女人拋棄的男人該有的淒慘樣子,但他一直等到那女人走了以後才表現出來,可見他其實自尊心很強,並不像他外表看起來那樣漫不經心,對什麼事情都毫不在意的樣子。
「是你!」男人的視線從落入眼中的黑皮鞋開始慢慢往上移,她戴了安全帽,但他卻一眼就認出了是她,「舒知威小子!」他叫她,黝黑的眸子裡閃過一絲狼狽的光芒。「你深夜不回家在路上遊蕩什麼?」
「我在找你。」舒知微取下安全帽,揉揉一頭亂得像鳥巢的短髮。
「找我?全世界的人都巴不得逃開我,你卻要找我?」他繼續用滿不在乎來武裝自己,「現在你找著了!怎麼,小子,我坐在地上的樣子看起來是不是很不賴?」
「俗話說好狗不擋路,你坐在路中間了。」她試著跟他半開玩笑。
「我不是好狗,是落水狗。」雷步森不以為忤地學狗汪汪叫了兩聲,接著又開始唸唸有辭了起來,仍是她聽不懂的悲傷,仍是跟之前同樣的調調。
「就算是落水狗也不該在馬路上亂吠,會妨礙安寧。」
「我沒有亂吠。」綁了馬尾巴的頭顱搖了搖,「那是一首拉丁古詩!」他露出自嘲的笑容。
「拉丁古詩?」舒知微從來沒有見過會讀詩的男人。
班上的男同學不是打籃球就是打電腦,除了教科書,他們連小說都懶得看,頂多看看漫畫吧,圖畫比文字多的那一種。但是雷步森竟然會讀詩。老實說,雖然她聽不懂他吟誦的內容,卻對其中傳遞的奇異氛圍有所感受。
「腔調聽起來很古板吧?」雷步森聳聳肩繼續自嘲。
「是有一種說不出的憂傷。」她緩緩地開口。
「你很敏銳,小子。」他仰起臉閉上眼,「譯成中文是這樣的……」他彷彿歌劇主角在吟唱著:「啊!我是這樣的疲倦;啊!我是這樣的衰弱,阮囊羞澀,一文不名!」他緩緩睜開眼睛,「很棒的古詩,把一隻落水狗的心情寫得淋漓盡致,你說是不是?」
「你不是落水狗,你是男人,應該在哪裡跌倒了就從哪裡站起來,而不是跌坐在地上自怨自艾。」舒知微試著鼓勵他。
「對一個被父親踢出家門,又被未婚妻拋棄,外加跌碎了骨頭的男人,你的要求實在太強人所難了點。」他誇張的說。
「跌碎了骨頭?」舒知微狐疑地瞄瞄那兩條癱坐在地上的腿。
「不是那裡,」雷步森故意曖昧地搖搖頭,咧開嘴,「是我的屁股。你也曉得,一個晚上來個好幾次,屁股沒跌到開花算是不錯了。」
如果他以為用「一個晚上來個好幾次」或是「屁股、屁股、屁股」之類的就能弄紅誰的臉的話,可就打錯算盤了。
「如果你在求職欄裡填上『擅長跌坐在地』,馬戲團團長看了說不定會考慮錄用你。」她說。
「這個主意不錯!馬戲團小丑或許挺適合我。」雷步森的眼睛一亮。
「當小丑你嫌太老也太硬了。」她立刻吐槽。
「你也知道我很硬?」故作驚訝的瞪大眼睛,雷步森刻意扭曲她的意思,見她終於臉色一僵,立刻樂透了似地用男人對男人的口氣說:「小子,」黑眸裡嘲諷的光芒熄滅了,「幫個忙好吧?」他用誠懇的口氣跟她打商量。
「我認識的硬漢沒有一個會開口求救。」舒知微連問都沒問他要她幫什麼。
「我不當硬漢,硬漢全是一群沒有腦子的蠢蛋。」
「不是硬漢也是蠢蛋的傢伙同樣比比皆是。」她動了動嘴唇。
「我想妳是拐著彎在損我是個硬不起來的蠢蛋。」雷步森自嘲地咧嘴一笑,接著假裝可憐兮兮地道:「可否請妳幫忙把我這個硬不起來的蠢蛋弄到車子裡去?」
沒辦法,人家都說得那麼白了,舒知微只好不情不願地過去把手伸到對方腋下,把自己當成人肉枴杖把他撐起來。
「我很重吧?」雷步森突然注意到人肉枴杖的臉蛋漲得紅透了。
「跟一隻豬比的話,你算輕的啦。」舒知微惡毒地回嘴,七手八腳地把落難貴公子扶進最貴的駕駛座。
跟豬比!雷步森沒想到會得到這種比喻,從來沒有人敢對他這麼大膽的說話。
「有你的,舒知威小子,真有你的!」但他卻挺高興跟豬為伍似的。
坐進車內扶住方向盤調好坐姿,雷步森望了她一眼,忽然有些狐疑地開口,「小子,我有沒有說過,你的嘴巴噘得很好看?」他咧著嘴問她。
「我沒有噘嘴!」但她噘著嘴瞪他。
「下巴還有個小酒窩。」他又抬起下巴比了比。
舒知微的臉紅了,那個小酒窩是她自認為全身上下唯一一個具有女人味的地方,可是別人常常看不見,沒想到雷步森卻注意到了。
「皮膚像水煮蛋又白又嫩,好像從來沒有曬過太陽。」他伸手想擰她的臉,但她臉一撇避開了。
撲了空的大手縮回來放在方向盤上敲了敲,望著她好一會兒,慢慢地,他看起來像是發現新大陸似的咧著嘴,接著露出一抹篤定的微笑。
原來她是女人哩!剛開始只是懷疑,現在則是確定,原來這個傢伙不是娘娘腔,根本是個弱不禁風的林黛玉般的女人。纖細的身材,柔嫩的肌膚,噘起嘴來十足的小女兒態,以及下巴中央那個帶著幾分性感的小酒窩;他竟然差點被她身上不合身的男性西裝給矇混過去,胡塗到一度連她的性別都搞錯了。
既然她不開口澄清,他也樂得繼續裝傻下玩下去好啦!
原本他已經覺得這個世界無聊透頂也絕望透頂了。被老爸逐出家門,到上弦月去買醉澆愁,然後又被未婚妻拋棄,他有足夠的理由一死百了,反正也不會有人替他掉一滴傷心淚,他那嬌媚的未婚妻不會,狠心的老爸更不會,至於這個穿著男裝的小天使……
他當然更沒有理由期待她為他掉眼淚!
人生苦短,笑比淚要重要得多。所以他是笑著離開那個家,也是帶著微笑撐著看他的未婚妻頭也不回地離去,那些他都咬緊牙關笑著面對了,何況只是一個萍水相逢的小女孩。她引起了他對人世間最後的一點興趣,一個穿著男裝的林黛玉,他沒必要對她擺出苦瓜臉,當然也沒有必要拆穿她,就當這是上帝跟他玩的最後一場遊戲,那他就玩下去好啦。
「你一直瞪著我幹嘛?」舒知微被他看得有些頭皮發麻。
「沒什麼。」雷步森若有深意地再看她一眼,那一眼更加堅定了她是女人,「謝了!」他沒有揭穿她的性別,只是簡短地道了聲謝。
「不客氣。」舒知微不願意把腦細胞花在研究他怪異的眼神上,他有瞪她的自由,她也有不理他的權利。逕自踅回去從機車肚裡取出牛皮紙袋過來,塞進駕駛座裡。
「這個還給你。」這才是她大半夜追出來等在這裡的目的,她只想把錢還給他,而不想管他被拋棄的事。
「把送出手的東西再拿回來,這不是我的風格。」
「我不能拿你賣掉敞篷車準備用來付信用卡費的六百萬。」原本她就不能拿,聽到那是他賣掉車子換來的最後一筆錢之後,她更沒有道理白拿人家的。
「那是兩碼子事!」貴氣十足的男性臉孔窘迫地紅了一下。
「我才沒興趣管你是哪一碼跟哪一碼。」舒知微堅持不肯收,只是乘機來個機會教育,「但你隨隨便便就刷掉六百萬,實在太離譜,難怪你父親會氣得把你掃地出門。」
「我爸不是因為我花錢才趕我出去的!如果妳有時間的話,我很樂意告訴妳我是怎樣惹火我老爸的……」
「我沒興趣!」她才懶得理他為什麼被踢出家門,但是……「如果令尊知道你連車都賣了,就是不肯去找個工作養活自己,還到上弦月去拚高消費,一定會氣壞了。」她忍不住數落他。
「大錯特錯!」雷步森沒志氣地開口,「他早就知道我沒救了。」
「沒救就沒救!」既然他自己都這樣認為,她更沒有必要跟他耗下去了,舒知微咕咕噥噥地轉身走開。
「喂!」雷步森又叫住她,「妳的錢……」
「我不要你的臭錢。」她只想趕快離開這是非之地
「這裡面全是白花花的新鈔。」他又說。
舒知微懶得跟他耍嘴皮,但突然想起他在離開上弦月時扔下的那句話。「什麼叫『你身上什麼都有,就是沒有錢的味道』?」她倒是想搞清楚這一點。
「意思是妳身上有一種純潔的味道,讓我忍不住想把妳弄髒。」雷步森坦白地說。
「你想用錢收買我?」
「看來我想錯了。」他承認。「沒想到妳會這樣做。」頓了一下,他又道:「妳讓人刮目相看。」他沒想過會遇到連白花花的鈔票都打動不了的靈魂,還騎著車把到手的鈔票往外推。
「你是錯了!」舒知微一點也沒有被稱讚的感覺,「我市儈得要命,我喜歡小費喜歡錢,但不碰來路不明的。」
「那是我正大光明賣掉敞篷車換來的。」
「不管你是賣車還是賣身,我不拿那種錢。總之,我跟你是道不同不相為謀!」她雙手插在口袋裡轉身踱開。
「妳到哪裡去?」雷步森著急地問。
「回家!」頭也不回地,她朝背後的男人擺擺手。
「把我一個人丟在這裡?」
說得好像她對他有應盡卻未盡的責任義務哩!
「你自己開車去醫院吧。」
再次揮揮手,她不準備帶走星星月亮太陽或任何一朵黑雲,傻瓜才會自己找麻煩,雷步森就是那個大麻煩。
「我的骨頭斷了耶。」
下定決心不理會那大孩子似的叫嚷,舒知微繼續往前走。
「車子也沒油了。」
「打電話叫加油站送油來啊!」她沒好氣地繼續往前走。
「手機沒電了!」雷步森不死心地叫道,「有電也沒用,沒繳手機費,已經被電信公司斷訊了。」
「那就去繳錢啊!」舒知微咬牙切齒地轉身,她真想打人了。
「繳了手機費,就沒辦法付信用卡費了。」
「你到底打了多少?」
四目相對,雷步森無辜的眼神讓她火冒三丈。
「也才二十幾萬而已。」
雷步森根本不知道民間疾苦,二十萬說得像二十塊一樣。
「你到底有沒有羞恥心啊?」舒知微不情不願的走回車門旁,「對一個陌生人說這麼多,你不覺得難堪嗎?」她瞪著他的眼神就好像他沒穿衣服在外面丟人現眼。
「我一點也不覺得妳是陌生人,反而覺得我們已經是朋友了。」雷步森咧著嘴說,「真的,我從來沒有一個晚上跟同一個人說這麼多話,妳是第一個就算講了這麼多話也不會讓感到我厭煩的人。」
「別以為這樣說會得到什麼好處!」舒知微沒好氣地哼道。
「看在我剛被未婚妻甩掉的份上,妳就多少體諒我一點嘛。」
「你臉上一點失戀的痕跡也沒有。」
「我的傷在心裡。」
厚顏無恥!他敢說她還真沒臉聽哩!舒知微不吭聲,等著看他還有沒有臉繼續往下說,想不到他還真有臉哩。
「真的,我發誓,」雷步森舉手做出起誓狀,「我對大胸部的女人一點招架能力都沒有。」
搞了半天,原來他留戀的只是那女郎的豐滿乳房而已。
「臭沙豬!」身為女人,舒知微忍不住替他的未婚妻抱屈。
「只是男人間的閒聊,幹嘛這麼生氣?」摸摸鼻子,雷步森明知故問地瞅著她,「妳又不是女人,幹嘛跟女人一樣愛生氣?」
「因為我就……」她把衝到嘴邊的話嚥回去。
「因為妳天生就是娘娘腔?」
他繼續逗她,覺得她鼓著腮幫子不吭聲的樣子真有趣。他忍不住繼續說下去,「抱歉抱歉,」他伸手朝她敬個禮,「我不是故意用娘娘腔來侮辱妳……」
「你給我住口!」這聲吼叫足以驚天地泣鬼神。
「喂,少年耶,現在是三更半夜耶!」二樓一扇窗戶被推開,頭上捲了幾個髮捲的中年女人探頭出來罵道。
「對不起!」舒知微這輩子沒這麼丟臉過,臉紅到耳根子去了。
「哼!」髮捲頭縮回去,窗戶關了起來。
「喂,娘娘腔,妳的臉紅得像蘋果!」
「我不是娘娘腔。」舒知微說完,就在雷步森低低的叫喚聲中憤怒的踱開。
她不承認她是娘娘腔,也絕不承認胸中鬱積的那口氣,泰半是為了他竟然到現在都認不出她本來就是女人。
除了頭髮短一點,身材平板了點,穿得稍微像個男人婆點,聲音頻率低了一點,除了那幾點之外,她的五官、她的長相……
好啦好啦,就算她從小到大當慣了男人婆好了,就算南部家鄉的父老兄弟姊妹,以至於大學裡的同學,包括她在班上最好的朋友金克勤也都當她是男人婆好了,這些她認了就是,至少男人婆總也是個婆,婆終究還個女人,而娘娘腔,再怎麼娘也終究是用來形容男人。
去他的男人!
有眼無珠!
欺人太甚!
★★★
憤怒的用力催趕機車油門,舒知微咬著嘴唇騎車回家。
那傢伙皮厚得要命,沒那麼隨便就摔斷了骨頭,他只是故意嚷嚷而已,她會理他才怪!反正就算手機沒辦法通,身上幾個銅板總是有吧,隨便找個公共電話求助都可以。那只不過是一條小巷子,又不是荒山野嶺,沒道理找不到人幫忙,而且雷昊群再狠也不至於讓唯一的獨子流落街頭而不顧。
所以啦,「哈哈哈!」她迎著冷風大笑幾聲,對著寂寥的夜空大喊:「沒必要良心不安!舒知微,妳做得對極了!」
就讓那大個子自己想辦法去吧!
有膽子到上弦月尋歡,有膽子把台北的小巷子當成「摸乳巷」,有膽子做就要有膽子當,雷步森再幼稚也得學會自己收拾爛攤子。
「原封不動把牛皮紙袋還給他,已經是仁至義盡啦!」她的嘴巴對著自己的耳朵說。
那傢伙沒有一點值得她牽腸掛肚的地方。
尤其是他花錢不手軟的方式活像……
活像一個毫無希望的……
將死之人!
舒知微猛然一驚,嘎地一聲,緊急煞了車!呼,好險,差點闖過紅燈,差點就被一輛呼嘯而過的大卡車攔腰撞上。
驚魂未定等待紅燈轉綠的過程中,她忍不住又喃喃自語:「那傢伙壞是壞,但應該還不至於會笨到走上絕路吧?」
所謂好人不長命,禍害遺千年。
也許那個禍害還有的是辦法弄到錢,弄錢弄女人,就是那傢伙活著的目標,他都對那水蜜桃女郎說了:「真可惜,原本我想連這部也賣了,手頭上有一筆錢,跟妳過幾天痛痛快快的好日子。」
賣掉全台灣最貴的一部車,雷步森還是那個要什麼有什麼,出手闊綽的大少爺。
只不過像他那樣如流水般的花錢法,不消一個月,頂多兩個月,至少就能花掉上千萬,到時候還不是死路一條!
喂喂喂!好端端地,怎麼又想到「死」那裡去了!
總之不管是死是活,都不關她的事啦!
騎過一個又一個紅綠燈,經過一排又一排昏黃的街燈,夜已深沉,大地酣睡,只有二十四小時不打烊的便利商店和……
她實在不願看到,卻又不能不閉著眼睛騎車,不能不眼睜睜地騎過那間她經常光臨的加油站,不能不看見招牌還亮敞敞地向黑夜招手。
小子,我的車沒油了!
一陣低沉的嗓音忽然從四面八方竄進她的耳朵裡,接著又跳到另一句──
我開車技術好得可以一路開到天堂去!
別管他!管他要上天堂還是下地獄,管他是死是活。
硬催油門,舒知微逃命似地朝家的方向疾馳而去,眼看家門在望,眼看……
「可惡!」她詛咒一聲。
嘎地急轉掉頭把車騎進加油站,再沿著來時路騎回去。
不是因為她想幫他什麼!
只因為就算從南部北上念大學轉眼都三年了,她到現在還沒辦法改掉鄉下人急公好義的雞婆性格。
就算他是一隻迷路的狗,她這個雞婆的鄉下人也得確認他有沒有辦法找到回家的方向。
★★★
結果她錯了!
錯得離譜!
雷步森根本沒想過要找什麼回家的方向。
他就那樣大剌剌地、毫無防備地敞著車門,無懼寒流,歪斜在駕駛座上沉睡著,像死了一樣沉睡著。
「喂喂喂……」舒知微跳下機車,拿掉安全帽,伸手拍拍他的臉,「你醒一醒!」
但他就是沒醒來。
也許之前在上弦月喝了酒,酒的威力現在才開始發作,不過在瞥見車內扔得到處都是的空酒瓶後,舒知微很快就明白是怎麼回事了。
沒志氣的傢伙!
被未婚妻甩了,車沒油了,加上手機也斷訊的情況下,索性躲在車內喝個酩酊大醉。那些酒原本應該跟未婚妻同歡共飲,後來乾脆一個人拿來借酒澆愁!
她跟他說話,搖撼他,還掌摑他的臉好幾次,但他只是咕噥幾聲,卻沒有甦醒。
管他三七二十一,她都仁至義盡了,如果明天打開報紙看到社會版頭條寫著「台灣首富之子雷步森醉死街頭」,她根本連眉頭都不必皺一下。
但鄉下人就是鄉下人,她永遠學不會都市人自掃門前雪的冷漠,皺著眉頭,把那睡死了的傢伙設法拖到車後座,然後把油加了,接著繼續發揮「婦人之仁」,就地留下自己的機車,跳上那最貴的一輛車子,把他載回到自己居住的舊社區大樓。
就當暫時收容一隻迷路的流浪狗!
她是這樣想的。
萬萬沒想到,天亮以後,流浪狗會變成瘋狗狠狠地反咬好人一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