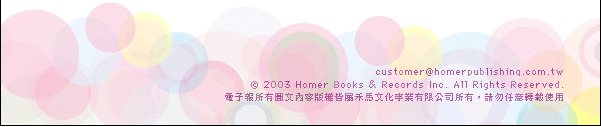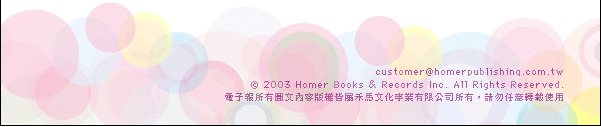一場婚禮,兩個新人,四位家長。
是誰婚了?肯定不是我。
回國後的第一場婚禮,只是序曲而已。
★★★
三月三日,良辰吉日,N城城南的大飯店,向陽漁港,對對新人即將攜手踏上人生的轉捩點,西廳的門外,簽到冊上是龍飛鳳舞的祝福,旁邊的大盤內堆滿紅紙包,灼灼閃人眼。
新娘的好友站在桌邊點頭微笑,對每一位來賓甜甜說:「謝謝。」桌下,穿著高跟鞋的兩腳不住地相互交換立地,這工作實屬累人。
突然,一雙肥嘟嘟的手伸到她鼻尖:「紅包九百九十九,討個彩頭,來,找俺一塊!」
新娘好友詫異抬頭,這人來砸場子的不成。
來人瓜子臉蛋,眼笑得直瞇,右嘴角的酒窩一閃一閃。
好友尖叫一聲:「熊貓!」飛快地從桌子一邊跑出來,拉了那人微肥的手指,有點激動,大聲說:「妳回來啦?」
也只有這人,明明瘦瘦高高的個子,手指卻是與常人不同,肥肥嫩嫩,越到指尖才越細下去,這麼大的人卻有雙孩子般的手。
熊曉苗,海歸,也是海待,畢業於美國俄亥俄州的某知名大學某冷門學系,碩士,昨天才回的國,回國第一件事:看人結婚。
「嗯,回來了,回國,回家。」她點頭笑,抓住昔日高中夥伴的手,佯裝凶狠:「一塊錢,拿來!」
對方比她凶猛,瞪了眼睛:「少來,妳既是新郎大學同學,又是新娘初中同學,份子不給我出雙倍!」
說完不爽,擰了她的臉頰:「別以為我不知道,請帖就是敝人寫的!趕緊給我找位子坐去,男方席,女方席,愛坐哪坐哪,隨妳!」
熊曉苗就這樣摸摸鼻子,灰溜溜夾著尾巴,去席間轉了一圈。她來得太早,沒什麼人,還是出去等。
站在廳外的後廊上給梅嬈打電話,大學宿舍的四小花旦之一──事實上一宿舍也只有四個人,梅嬈是唯一留在N城工作的姊妹。
彩鈴是小強曲,在一聲「好吧,叫我漂亮姊姊接電話」中,熊曉苗鑑定此人猥瑣的本領這幾年更上一層樓。
電話最終被接起來,那人驚訝的叫:「妳回來啦?」
好吧,她早已習慣這樣的驚訝,可是她明明上個星期還在MSN上和此女聊天告知近期回國,託她接受喜帖。
但她還是很愉悅,廊外細水小橋,這樣的喳喳呼呼聲已是久違五年。踢著牆邊的鵝卵石,她說:「嗯。在幹嘛呢?我都到了!」
梅嬈正在門口穿鞋,拎了高跟鞋,夾了耳機,說:「別急啊,要好好準備,參加婚禮就是變相相親。」
熊曉苗對她這相親達人的理論很是無語。
梅嬈拿了包下樓,高跟鞋「嗒嗒」作響,笑說:「熊貓啊,要知道這麼幾年,南京的咖啡店沒人比我還熟悉了!」
熊曉苗捏了手機笑,口裡直說:「是是。」
梅嬈開了車門,換了耳機,說:「對了,下次一起去相親吧,姊妹兒,帶妳介紹個好的!」
熊曉苗也不知她說的真假,胡亂答應。這人鬧起脾氣比誰都厲害。
梅嬈開車出門,嘴上胡說,突然來一句:「曉苗,妳這次回來有沒有想過見他?」
熊曉苗本來說話說得好好的,她突然這麼一問來了個措手不及。梅嬈的思維向來是跳躍性的,比青蛙還厲害,她早知道的,只是聽到她提,還是吃了一驚。
今日,天氣正好,早春的太陽照在臉上,毛茸茸的溫暖,小池裡幾尾金魚優閒地擺動,她蹲在池邊,慢慢看。
怎麼可能不想他?怎麼可能不想見他?
在這五年裡,他做著什麼樣的工作,和什麼樣的人打交道,住著什麼樣的房子,她都偷偷想過,越來越少地想起,卻是不能忘懷的牽掛。
想見到他,卻又怕見到他,怕見到他過得不好,她會難過;他過得很好,她也會難過……沒有了她,他依然可以很好,不是嗎?
越是想念,也越是怕遇見。
梅嬈車前邊的交通燈轉綠,她繼續開車,吸了口氣,高聲問:「那在哪相?身高要一米八的?」
熊曉苗摸不著北,「啊」了一聲。
梅嬈咬牙切齒:「妳剛才答應的啊!說,相親地點,有啥要求沒?」
熊曉苗失笑,無奈地說:「隨便妳啊,地點隨意,身高隨意,著裝隨意,大家隨意!」
梅嬈握緊方向盤哈哈笑,那一瞬間,她想起大學剛進校,她拉了一個女生問哪裡找竹竿掛風扇,那女生傻傻地看她一眼,說:「我去外邊撿的樹枝!」
五年過去,梅嬈握著方向盤,看著前方,笑得肆意,突然覺得那個傻里傻氣的熊曉苗還是回來了。
熊曉苗掛了電話,準備走去大門那等梅嬈,想想她開車來也差不多了,正站起來準備往外走,當她轉身看見廊下站著的熟悉而陌生的身影,突然不能動彈。
她想梅嬈真是個霉嘴,現在不是想不想遇到他,而是已經遇到他!
在她還沒做好思想準備,不知道做什麼樣的動作,勾起多少度的嘴角的情況下,就那麼惡狠狠的遇見。
她想,或許給她再多的時間,她依然還是不知該以何樣的狀態去面對……
春日的和風掠過他的眉梢,爾後,擦過她的眼角,她閉了閉眼,風裡夾雜了濕氣,染上眼角。
他靠在迴廊下,五年前的青澀少年,現在已變成稜角分明的成熟男子,銳利的眼鏡遮住清澈的大眼睛,閃著鋒利的寒意。
她知道他的長相向來都是人群裡一眼望去就見他的,現在依然,卻像換了個人般,犀利,尖銳,如同毒藥。
夏靜生,二十一歲起,他的名字刻入她的命。
恍惚地想起那日的陽光也是不輸今日的溫暖,記憶裡的大學校園,杜鵑花開得正好,老香樟的味道瀰漫不去,嬌俏的女孩,拉了男孩的手:「小靜,小靜,你看,你叫小靜,我叫大雄,我們是不是天生注定在一起?」
下課的時候校園裡總是喧鬧非凡,周圍是來來往往的人群,男孩微惱,耳根盛開淡淡的紅暈,咬牙低語:「熊曉苗,妳再喊我小靜試試看,妳也就是個偽大雄!」
嘴裡邊罵著,手卻是輕柔的,指尖撥去女孩頭上的花瓣,如春風般的輕柔,以至於女孩都沒有注意,還是在咕噥。
人來人往的,有人回頭看了一眼,男孩窘了,手中的「流體力學」招呼上去。
女孩「啊喲」叫了聲:「夏靜生,你打我腦袋幹嘛!」
曾經,他也是大學裡的天之驕子,沒有這樣一副冰冷的眼鏡,卻有著柔軟的髮,緊握她的手的溫暖大手。
而今,他上了定型的髮彷彿根根分明的堅硬,陽光在髮梢鍍上金屬色。
她才發現他今天的打扮極其正式,綢光的西服,寶藍色的領結,猶豫了半天,想開口的「你好」吞回肚子。
人生真是諷刺。他說過的話彷彿還在她耳邊,她記得他喜歡的電影,她到現在還不敢再聽他曾唱給她的歌,她在美國走遍超市,只為找最接近他喜歡的黃紙包檸檬味的糖果,這樣的兩個人,數年後再見,卻是在別人的婚禮,抑或是,他的婚禮。
今日真是個好地方,向陽漁港結婚的新人一對對也太多了點。
她扯嘴笑,說:「恭喜。」
說完在心裡罵自己的醜樣,言不由衷,連自己都要瞧不起自己。
可是,她除了「恭喜」,還能說些什麼?
頭別向一邊,耳裡是流水的「沙沙」聲,怕一低腦袋,眼淚就要流下來了。
良久,他說:「不是我的婚禮,做伴郎而已。」末了,加了句:「妳就那麼希望我結婚?」
聲音涼入骨髓,彷彿血管裡都密密地冒出汗來。
她不敢說話,無所適從,偷偷瞄了眼,才發現他手裡握了瓶紅酒。也對,哪有新郎結婚拿著酒瓶滿場跑的。她這才想起新郎是他的大學室友……
與他的相遇太過突然,幾年的擔心、緊張,一見面就想到最壞的情況。
想來,是她自找的。
如此埋怨著,心裡卻舒暢了點,但還是為他的冷意所傷,雖然是她咎由自取,但這樣的話聽在耳裡是心痛的。
她以為就算不能在一起,還是能做個普通朋友的。後來想來,是她幼稚。愛啊,恨啊,永遠都沒一句陌生人般的「你好嗎?」來得虛偽傷人。
如果再相遇,請不要問我「你好嗎?」你到底是想讓我答「好」還是「不好」?
她低聲說:「對不起。」聲音微顫,不僅僅是為了她的誤會。
他變了臉色,眼裡似要噴出火來,咬牙切齒:「熊曉苗,妳不要和我說對不起,妳說對不起是對我感情的侮辱,妳不欠我什麼,我心甘情願的!」
她抬頭想看他的臉,卻只看到他挺直的傲然的背,快步消失在轉角。
陽光有點刺眼,她捂了捂自己的眼睛,跟著,也慢慢走出廊去。
很快地,梅嬈就來了,偷偷摸摸告訴她:伴郎是夏靜生。
熊曉苗嘆氣。唉,這話早該說的。算了,咧嘴笑笑,看著站在新人旁邊,身後跟著臉圓乎乎的可愛伴娘的他,這也是她與他最後的遇見了吧。
夏靜生,我們這輩子太多的遇見,太多的錯過,一不小心就把緣分用過了吧。
★★★
梅嬈和熊曉苗入席,新人說話,男的是劉峰,微胖,老好人一個。熊曉苗那時跑夏靜生宿舍跑得勤,老叫他「瘋牛」。女的是韓薇,瘦小的爽朗女孩。
一個是她的初中同學,情緣是一起攜手上過廁所。一個是她的大學同學,成天說:「小靜老婆,我請你吃飯,但是你們夫婦先請我吃頓飯。」
這樣的兩個人,如今成長,如今攜手,生活真是很奇妙的事情,熊曉苗不由感嘆。
啪啪地鼓著掌,眼角泛紅,昔日一起成長的夥伴,如今能夠一起幸福,世上最美的事莫過於此。
熊曉苗興奮感動之餘,卻沒有發現伴郎瞥了眼她泛紅的眼角。
夏靜生其實本不願意當伴郎,但他是媒人──天知道這完全是巧合。一個是他大學室友,一個是高中同學在酒席間偶遇,一個大男人怎麼會喜歡做媒婆,他只是禮貌性地介紹,原來萬事都有著因果。
他不經意地瞥過她的眼,習慣了在人群中望向她在的地方。
這個笨蛋,和以前一樣,老是為別人的成就而感動得像自己的事一樣。
他是知道她要過來的,劉峰打過電話說給她寄了請帖。他在那頭沒有說話,心慢慢收緊,劉峰卻以為他是不想見她,趕緊說:「她沒回來,找梅嬈代收的,估計是回不來。」
天知道他有多少次盼望著她回來。她QQ的簽名一換再換,他一看再看,看到她的「三月回國」,他的心再一次狂跳起來,如同毛躁的少年,坐立不安。
她走後,他不是沒有勉強過自己,只是沒辦法,也就隨著性子下去了,直到有天有人問他:「你是不是還在等她?」
他才恍然大悟,原來他是在下意識的等待著。即使時間長了,他自己都不知道在等什麼,他,還是孑然一身。
心中無法再有人似她一般了,如她一般笑起來有小小的酒窩,呢喃地喊他:「小靜。」
一生的熱情彷彿在和她的歲月裡花光了,再也提不起勁來。
曾經,他想過畢業,成家,有了她在身邊,如何的苦都不算苦。
爾後她走,可是生活還是要繼續,少了個她,他還是一個頂天立地的男人,他夏靜生依然要過他自己的人生。
只是,午夜夢迴,他還是會想起她的笑顏。清除了她的一切,卻無法把她清掃出心口。
前幾年的時候,他想過她回來,依然會笑著喊他,她玩笑著提大雄和小靜的故事,然後他就可以名正言順地欺負她,臉板著,心裡卻漾著笑,慢慢流下眼淚。
他這樣千百回地想過,直到他無力去想。
笨蛋大熊,我沒有忘記妳,如果要回來,請快一點,別老讓我等。
今年我在等妳,下一年我還是會等妳,這一生,我固執地等妳……
我很想這樣一直等下去,但,終有一日我也會渴望有個溫暖的家,有趴在膝頭的孩子喚我「爸爸」。即使我可以忽略這一切等下去,這個世上還有件事叫「生老病死」,我會恐慌在自己有限的生命裡等不到妳。在垂垂老去的那一刻,我依然等不到妳,怎麼辦?
我固執的決定等妳,可惜歲月不等我,終有一日,我們會敗給生活,敗給時間……
熊曉苗,我沒有忘記妳。如果要回來,請快一點。別總是讓我等,再晚,我怕一切都回不去了。
這一天,他終於等到她。看著她蹲在池邊,他握酒瓶的手指不自覺地緊縮,聽著她熟悉的聲音越來越近,聽她說要去相親,他突然意識到自己忽略了這五年的變化。
他在等她,但她是不是肯走回來讓他等?
說實話,變的何止是她,連他自己都認不得自己,直到再見她,所有的記憶湧上心頭。
意識到這樣的變化,他的心慢慢冷卻下去。
他不懂她的腦子,竟然以為他是新郎!很好,好得很,他從來都沒想到「恭喜」這話可以讓人如此地恨入骨髓。
別說他沒想結婚,即使結婚,他也不會請她,他受不了他的婚禮,她坐一席。
有人說癡情之人必有絕情之處。如果他要成家,不是和她,那麼他這一生將不再見她。他忘不了她,但可以不見,就這樣放手,因為他是一個家庭的責任。
他從來就不要她的「恭喜」。
他更沒想到等來等去,等到的是她的「對不起」。
這一輩子,他夏靜生最不要聽她熊曉苗說兩句話──謝謝、對不起。
他不要她的「謝謝」,他為她做的都是甘心情願,她好,他就好。
他不要她的「對不起」,她給的傷如同她給的笑,他都好好記下,她說對不起,是對他付出的侮辱。
他站在笑得美滿的新人後面,向她看。曾經他也以為他們可以這樣,可惜不是。
他不信命,但人說善惡終有報,如果是他促成了這段美好姻緣,那麼老天看到,是不是也可以還他一段美好?
★★★
酒席開始,熊曉苗破罐子破摔,打擊大了,菜拚命吃,酒來者不拒的喝,豪氣無比,就差沒捲袖子了,居然還划了酒拳,說:「我乾,你們隨意!」
隨意個鬼,又不是男人。
梅嬈在一邊都後悔死了,邊擠著笑邊往旁邊挪。她怎麼和這樣一個人坐一桌?看看身邊男士的菜臉,她也知道這場群眾相親黃了……
梅嬈同志終於在沉默中爆發,捏了熊曉苗的耳朵吼:「熊曉苗!猴子變成人類要一萬年,妳這熊貓再變回猴子只要一瓶酒!」
說完,看了眼對面坐的某英俊男士此時快跌落的下巴,臉紅了紅,拉了熊曉苗閃人。
熊曉苗被她拉得一暈一暈,跌跌撞撞,一不小心碰上正在敬酒的新郎,立正站好,對新人鞠躬,聲音居然很平穩,說:「祝福你們!」誠懇至極,完全不似醉酒之人。
梅嬈拉她,陪笑說:「不好意思,她醉了!」
熊曉苗很認真的掙脫她拉著的手,對新人揮了揮手,說:「Bye-bye!」
說完,又望向伴郎的黑眸,說:「再見!」
觥籌交錯的酒席,穿紅衣的新人邊,一個酒醉的紅臉女人,一個眸光閃耀的英俊伴郎,相望無語,氣氛詭異無比。
她轉頭往外走,一步步,沒有回頭。
他說:「再見。」聲音輕得只有他自己聽見。
再見,再見,再也不見,抑或是,再次犯賤?
★★★
過了幾天,某個月黑風高的晚上,接到梅嬈的電話,這女人一頓暴吼:「死熊貓,趕緊到華僑路的常青藤來!現在,馬上!」
熊曉苗嚇了一跳,二話不說,趕緊打車出門。
推開餐廳的大門,看見梅嬈女士正儀態端莊地坐在那裡,走過去,正好和離席的戴眼鏡的斯文男士點了個頭。
在男士離開的位子上坐下,看著梅嬈在昏黃的燈下畫得精緻的妝,熊曉苗想笑又不敢。
梅嬈拿小湯匙敲咖啡杯沿,數落她:「叫妳來相親,妳也沒來。小姐,妳想怎麼樣啊!」
熊曉苗莫名其妙,問:「什麼時候啊?」
梅嬈頭也不抬,理都不想理她:「自己看手機!」
熊曉苗拔出手機,一看,果真有好幾條短信躺在那裡。天啊,她一向都沒有留意短信的習慣,在家看看電視,收拾下房子,哪裡會注意!
一時氣短,陪笑,問道:「嘿嘿,我真沒看到。剛才相得怎麼樣?」
梅嬈「哼」了一下,說:「沒感覺!」
熊曉苗樂了:「剛才那人挺好的啊,什麼叫沒感覺,感覺是可以培養的!」
梅嬈拿小匙指她:「少來這套。什麼培養,當拍電視劇啊。我現在都對他沒感覺了,以後要真結婚,這五十年,難道像『大話西遊』裡一樣,說『吐著吐著』就有感覺了?放屁!」
熊曉苗笑死了。梅嬈這幾年都相了無數次親,換了N個男朋友了!
梅嬈每任的男朋友都是傳奇,宿舍裡的人都告訴她了,上任分手的原因是那人不知道什麼是哈根達斯;上上任的分手更好笑,那男的不是南京人,跑來看梅嬈,兩人去逛街、吃飯,路過南京的萊迪商場,其實就是個兩層的地下流行廣場,裝修很有格調就是,那男人說了句:「我靠,南京居然有那麼大的小商品市場!」梅嬈二話不說,回去就和人分手了。
熊曉苗捏了捏鼻子,看梅嬈,淡淡的眼線,鬈翹的睫毛,細緻的粉底,那個大學裡一開始連抹防曬霜都嫌費事的女生,現在就是個精緻的女人。
她回憶梅嬈剛離去的相親對象,突然想起梅嬈大學時的男朋友。
那男生不是特帥,卻戴了眼鏡,很是斯文,確實人也是個才子,彈得一手好鋼琴,每次晚會演出都有他,還組了樂隊,風光無限,把梅嬈這個青春飛揚的女生迷得暈頭轉向,夜夜都是聽著那男孩寫的情歌入睡,夏日裡買了西瓜都是自己一半,再給他一半,切好了送去。
可聽說畢了業以後,那男生去了北京闖蕩,而梅嬈,留在了南京,不停的相親,不停的戀愛。
熊曉苗沒有問梅嬈有沒有忘記了他。如果忘記,為何要老是找眼鏡男相親?但如果不曾忘記,為何要一次又一次的戀愛?
熊曉苗在美國的時候也曾打電話給宿舍的其他兩人隨便聊聊,保持聯絡,一次談及大學中的趣事,宿舍的楊希不經意地說:「記得那一班的班花嗎?」熊曉苗說:「記得,怎麼了?」
女人對八卦往往都無比敏銳,楊希說:「人家現在都在老家結婚了!」
熊曉苗興致勃勃,說:「真的?是和老盧嗎?」老盧是大她們一屆的學長,當年這兩人的戀情也是轟動一時。
楊希「嗤」了一聲,說:「那都什麼時候的事了。兩人沒畢業時就分了,老早的事了!」
熊曉苗是沒畢業就離開的,所有的記憶都在離開之前,聽她這麼說,不由一愣。
原來只有她還停留原地……
她想,有的時候,真不知道是歲月拋棄了她們,還是,她們拋棄了歲月。
所有的美好都變成了曾經。
梅嬈喝了口咖啡,低聲說:「曉苗,就這樣了。妳和夏靜生最後都變成這樣,我還能相信什麼呢?」
畢業越久,就越覺得世界和想像的不大一樣。工作如此,友誼如此,戀愛更如此。
總以為世上還有這樣一對幸福的,總以為哪怕所有的人都分手,還有這兩人是在一起的。可是,如今連大熊和小靜的故事都不存在了,她還可以相信什麼?
梅嬈到現在都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那年,是夏靜生那邊先有新加坡的建築公司要簽他去工作,熊曉苗知道後,一天沒有吃飯,晚上的時候下樓,半夜是哭著回來的。梅嬈就見她這樣魂不守舍的過了一段日子。哪知道最後變成熊曉苗走,說是父親打算移民,要她先過去讀書,幾天後就走了。
最後,反是夏靜生拒絕了那份工作,留在了南京──熊曉苗出生的城市,很多人走了,很多人留下的城市。
這都是什麼事兒啊!
熊曉苗聽她說完,不再說話。
事實上她也想問夏靜生為何留下。在出國的頭幾年,她都想回來找他,夢中的時候,一遍又一遍的回憶。
那個夏夜,天上的月亮幾乎透明,泛著蒼白的光,細密的葉在風中搖擺,那棵宿舍樓外的鳳凰樹下,他在此處幫她拎過無數次的水瓶,等她上過無數次的自習,也曾在樹下,細膩地親吻著她的額頭,然後哄她:「快上去睡覺。」
那夜,他的手插在口袋裡,燥熱的風掀動他的衣角,他說:「熊曉苗,妳不能那麼自私。」在寧靜的夜裡,他微涼的聲音敲打著她的心,她就那樣邊跑上樓邊拿手背狠命擦著眼淚。
她為自己的衝動懊惱。當年年少氣盛,聽他說她自私就委屈得不得了,以為就這樣分了手。她也很想問他為什麼不去新加坡了,可是所有的問題,在歲月的流逝中,都變得說不出口。
五年前,她可以選擇不去,但她沒有留下。
五年中,她也可以選擇回來,但她不敢面對。
這世上有種東西叫做「過去」,一旦過去,就回不去了。
那個人,他曾是那麼慷慨地等待妳,他本來是妳的,妳自己選擇不要,那就永遠不要可惜。世上有很多東西是可以挽回的,譬如良知,譬如體重。
但是不可挽回的東西更多,譬如舊夢,譬如歲月,譬如對一個人的感覺。
梅嬈想想,狀似不經意地問:「親愛的,說老實話,見到夏靜生是什麼感覺?」
熊曉苗聽她提夏靜生,心突地一蹦,眼皮跳了下。這麼多年了,依然這樣。
再見到他,是不是真的可以放下,就這樣算了?
她看著梅嬈那狡黠的眼,搖頭晃腦:「真是,眾裡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瞄瞄對面的八卦臉,嘆:「那人依舊對我不屑一顧啊!」
梅嬈睜大眼,氣罵:「滾!」
起身,她捏了掐熊曉苗的臉,晃了車鑰匙,說:「走吧,姊妹兒送妳回家!」
熊曉苗笑,她想她怎麼認識林深深這樣的人,還能和梅嬈變成莫逆之交?人生真是奇妙。
她想每個人對感情的態度都不大一樣。比如林深深,放棄了或許也是一種幸福。比如梅嬈,放棄不了,就在一個又一個的懷抱中渴求溫暖。比如她,臉上笑著,心中卻有癒合不了的痛。
多少人因為寂寞而錯愛一人,又有多少人因為錯愛一人而寂寞一生?
★★★
告訴大雄我愛她(下)節錄──
是什麼時候開始的呢?
初到美國的第一年,她夜半的時候開始胃疼,赤著腳起床,給自己倒一杯水,捂著肚子在床上輾轉反側,告訴自己要早點睡覺了,明早有課,可還是冷汗直冒。
咬著牙,想起父母的叮嚀,有點心酸。
想起曾經那個人,他有璀璨的眸,半夜跑到她宿舍樓下,隔著門遞給她胃藥;想起曾經那個人,他有溫暖的手,嘴裡罵著:「誰教妳不聽話!吃了多少冷飲?」臉上流下汗來,手還是在幫她揉著胃的。
想起曾經那個人,他有醇醇的聲音,她在電話裡疼得沒力氣,憋了聲音說:「小靜先生,我胃疼!」他從學生會的辦公室溜出來,坐在大學生活動中心外邊的臺階上,或許是皺了眉的,或許是好笑的,放在電話裡卻都變成:「乖,我陪妳說話,說完就不疼了,好好睡覺。」
她在這樣的夜裡,想起以前的種種,恨透了自己白天吃多了自助餐──留學生永遠對「自助餐」三個字無法抵抗。
每一次胃疼,就會想起那樣一個人。記憶的輪廓慢慢浮現,人變得特別的脆弱。
黑暗中去摸索手機,點下了開鎖鍵,一圈光亮刺著了眼,想想誰若是這時候進來,肯定以為是貞子再世。她為自己這樣的想法起了笑意,但不到幾秒就收斂了,心裡罵道:熊曉苗,妳真是甩到無敵!
一個個名字翻下去,越來越快的翻動,越來越沒耐心,最後,愣在一個號碼上。
只有一串號碼沒有名字,因為老是刪去了又加上,乾脆不寫名字了,可即使不寫也知道是誰的號碼。
心顫顫的,伸出指去,突然想起──忘記買電話卡了。
她苦笑著,想到葉子曾在一個聚會上問過:「你們有沒有過特別想找人說句話,但翻遍了電話簿找不到這樣一個人的時候?」
文樹點頭,胖子一笑,一抬手一杯下肚,她那時說:「還好!」
其實不是還好,只是因為初來乍到,沒來得及遇到這樣的情況。
悶著把手機拋開,她繼續捂著胃皺著眉。
好吧,好吧,總有一刻會不疼的……
不知是什麼時候睡著的,只記得天亮的時候她一睜眼爬起來,趕緊刷牙、找書,上課去。
坐在教室裡,她笑著和旁邊的朋友打招呼,教授的PPT翻得比誰都快,她刷刷的抄,昨天的脆弱早來不及想起……
★★★
有人說:「我不寂寞,因為我習慣寂寞。」
看似堅強的盔甲,實則一擊即碎……
熊曉苗又一次想起胃疼的事情。人總是吃過苦頭才會學乖,在後來的幾年裡,她都盡量忌口,吃東西時也注意很多,胃慢慢調整過來。沒想到最近胃沒問題,卻還是應了流行,感冒了。
看著坐在一旁抿嘴開車的夏靜生,偶爾遇到紅燈停下,就會伸出一隻手,貼在她的額上。
她笑,拉了他的手下來說:「我只是感冒而已,你再摸幾次還是發燒,別摸了!」只是不忍心他擔心。
他卻是瞪了她一眼,蹙起秀氣的眉來,大眼裡閃過一絲惱怒,咕噥著:「還和以前一樣,不讓人省心!」
她點了點暈暈的頭,嘿嘿的笑起來。
要老像以前一樣,她在美國的時候早把自己整死了。
只因為以前有他,於是什麼都不怕,儘管糟蹋,反正他會心疼。因為以前有他,所以不用計較,什麼東西都傻傻的,因為有了他就是她熊曉苗一生最大的財富。
呵,只因為以前有他啊……
省人民醫院似乎什麼時候都是繁忙的,有落地窗的大廳,匆忙的人群,護士小姐坐在導醫台邊,笑得卻讓人心慌。
夏靜生牽了熊曉苗去掛號,本來只是看個感冒,掛水開藥的,想了想,有禮的對掛號小姐說:「掛個血液科,查個血全套!」
熊曉苗傻問:「為什麼要抽血?我就感冒而已!」
夏靜生偏了頭:「妳老愛吃甜的,順便查查血脂。」
熊曉苗托著她暈暈的頭,想說查血還有順便的?又不是超市大買賣。這人就是不好心,要她挨一針!
她還沒抱怨完呢,夏靜生又像想到什麼似的,側了漂亮的臉說:「再掛個骨科。」
回了頭,卻不望她,自言自語:「前幾天不是說腰疼?一起看了!」
熊曉苗臉紅。雖然夏靜生說的聲音不高,但大庭廣眾的,一對年輕夫妻,男的說「妳腰疼!」還是引人遐思的,梅嬈就嘲笑過她,簡直想死的心都有了!
她敢怒不敢言,惡狠狠的踩了夏靜生一腳。
夏靜生可不管,對著正低頭偷笑的掛號小姐微微頷首,禮貌一笑:「謝謝。」
小姐一個臉紅,掛號單刷刷的打出來。
熊曉苗決定和夏靜生這個變態劃清界限,夏靜生拿了一沓的掛號單,翻了翻,說:「去看感冒開藥,骨科的號在前邊先去看骨科,再去驗血、拿藥,最後……」
站在人來人往的大廳裡,他低著頭,柔軟的劉海微微的散下來,垂了長長的眼睫,仔細研究,遠遠看過去就是個雅致的男人,說出的話卻像個管事的小老頭子,要真有人走近聽見他在說什麼,估計會吐血。
熊曉苗正咧了嘴笑呢,夏靜生就抬起頭,臉紅起來,吼她:「不許笑,醫院裡要嚴肅點!」
拉了她往內科走,突然回了頭,倒自己笑起來說:「現在,出發!」
熊曉苗嘴角笑得歪啊歪,頭轉啊轉,心裡卻美啊美。
這夏靜生倒是越來越可愛了。
★★★
看完骨科,拍完X光片,等片子的時候正好去抽血。
熊曉苗這輩子就是個沒出息的,愛吃,躲懶,怕疼,但也遇上了夏靜生,命中注定是不得安生,攪不過他,只好硬了頭皮往抽血的窗口一坐。
屁股還沒落下去,夏靜生就把她拽起來了,以為是他良心發現了,他卻是把她拎到另一張凳子上坐下,雲淡風輕的說:「找個年紀大的醫生,有經驗,不疼。」
她看看剛才窗口,蘋果臉的小護士,紅了眼睛扎針,臉一抽,就覺得自己的膀子疼起來。按她自己的邏輯,肯定是找可愛系的。幸虧啊,幸虧。
望了望自己面前的這位馬臉大媽,她問:「阿姨,抽得疼不?」
大媽面無表情的搽碘酒,說:「怎麼可能不疼,怕疼別抽啊!」
熊曉苗「哦」了一聲,低頭想了想說:「阿姨,盡量少點疼,謝謝啊!」
夏靜生在一旁聽著好笑極了,看她可憐巴巴的伸出雪白纖細的手臂,直嚥口水,還在那左一個阿姨右一個阿姨的,怕大媽真煩了,狠狠給她一針,叫她閉嘴,扶了她頭站好。
熊曉苗覺得蟲子螫一下的疼,知道針頭進去了,害怕大媽抽到了空氣,她又要挨針,趕緊回頭,一看管子是空的,苦了臉問大媽:「阿姨,妳沒抽到啊?」
馬臉大媽的臉貌似更長了,沒好氣,鬆了皮筋,說:「怎麼沒抽到?」褪掉針管的外殼,深紅的一管血,沒好氣說:「這是什麼!」
熊曉苗嘿嘿笑,剛才那殼子居然是不透明的,白色的外殼,她一看嚇了一跳,以為是沒抽好,還好還好。
夏靜生笑她,她拿了棉花按按膀子,甩甩很沉的頭說:「這有什麼好笑的!都和你說了抽血不疼!」特意強調了「不疼」。
到了骨科看片子就來事了。醫生說:「腰沒傷到,只是尾椎骨那兒有點發炎。」指了指片子上腰下的一塊骨頭,說:「就這邊,有點陰影。」
熊曉苗和夏靜生一看,果然是。夏靜生問:「醫生,有什麼藥或辦法能治好?」
那醫生看了眼熊曉苗說:「妳是不是常常坐在電腦前?」
熊曉苗點頭。只要在家,她都是在電腦前,維護網站啊,看電視啊,發帖的。
醫生也點頭說:「很多白領年輕人得這病,可以開點中藥。」又瞟了眼熊曉苗一副萬事大吉的樣子,不緊不慢說:「但是要注意,坐久了要起來運動,不然老了會發展成骨質疏鬆,癱瘓也有可能。」
醫生推了把眼鏡,低頭開藥。
熊曉苗嚇得不說話,這醫生太能嚇人了。夏靜生皺了下眉頭,點頭對醫生說:「謝謝。」
才出了骨科,夏靜生就一副烏雲籠罩的樣子,說:「熊曉苗,妳趕緊去給我找份工作,不許老待在家裡!」
熊曉苗哪裡肯,家裡多舒服,搖了夏靜生的手,說:「我在家,保證不老坐在電腦前!」
夏靜生板了臉說:「不行,對妳是不可能的事!」他太了解熊曉苗了,說是這麼說,估計就認真貫徹個幾天,以為好了,就又開始宅了。
夏靜生說:「妳不找,就到我們公司來坐著!」
熊曉苗晃晃暈乎乎的腦袋說:「那不行!」去他那不如自己找。她氣了,說:「我在家也是有工作的,又不要你養!」
夏靜生冒火,手都快掐上去了,「我還養得起妳!妳要在家?行,我去把電腦都扔了,咱們過原始生活!」大不了他的工作在公司做完。
熊曉苗一見夏靜生認真,就知道沒戲。雖然平時小吵小鬧,最後都是他讓她,但大事他是絕對的權威。
沒戲的結果,就是在沉默中抵抗。
夏靜生想到熊曉苗感冒還要多喝水,心下是火大的,還是想著她好。
軟了聲音問:「想喝什麼?」大丈夫能伸能縮是好本事。
熊曉苗懶得理,說:「隨便。」
男人一聽隨便就頭疼,夏靜生問:「那,礦泉水?」
熊曉苗說:「不喝,沒味道!」
夏靜生捺了性子問:「果汁?」
熊曉苗說:「太甜!」看著他明明想咬死她,還是憋脾氣問她的樣子,她倒忘了生氣,心下偷笑。
夏靜生壓了壓細長的眉角說:「那妳想喝什麼?」有點咬牙切齒。
熊曉苗攤了手說:「隨便!」無辜至極。
又隨便!夏靜生一火起來,乾脆不理她,自己轉了身就走。
熊曉苗趕緊拉住他衣服,擠了一臉的傻笑,湊到他氣壓極低的俊臉面前說:「小靜先生,別生氣啊!」
夏靜生哼了一聲,繼續不理。
她諂媚的拉了他細長的手指說:「我喝果汁行了吧!」
夏靜生斜了眼丟給她句:「喝什麼?蘋果汁?柳橙汁?」說到底她是病人,不和她計較。
熊曉苗嘿嘿笑:「喝蘋果味的柳橙汁!」
夏靜生也很鎮定,說「好」,冷冷一笑,倒也是魅惑無比的狠勁兒,爾後,悠悠的亮了白花花的牙說:「我咬死妳算了!」
★★★
修養了幾天,熊曉苗就被梅嬈小姐拉出去閒晃了。
在德基下邊吃飯的時候,熊曉苗想到梅嬈前幾日提不起勁的樣子,隨口問:「最近相得怎麼樣?」說完又想笑,這話都成了和梅嬈打招呼的專用語了。
梅嬈不說話,半晌抬起頭,眼睛很亮,臉微紅,低聲和熊曉苗說:「熊貓,我最近碰到他了!」
熊曉苗愣了下,問:「他?蔣仲文?」
梅嬈這麼興奮而嬌羞的說起的,只會有一個人。
梅嬈點點頭,吞吞吐吐說:「他問我要了手機號碼,還要我給他個機會!」
熊曉苗朦朧中想起大學裡那個彈鋼琴的才子,為梅嬈唱情歌的眼鏡男,突然間回到了那個白衣飄飄的年代。
她笑得促狹,問梅嬈:「那妳怎麼想?」
梅嬈低頭說:「我不知道!」嘴角的笑已經掛著。
這樣的不知道,卻是已經有了答案。熊曉苗想著,只能在心中為好友加油,畢竟她和夏靜生有今日,也希望所有沒能在一起的情侶能夠有這麼一天,更何況是感情一起發芽的梅嬈。
笑笑鬧鬧,邊吃邊問:「他不是北漂了嗎?怎麼回來了?」
梅嬈嘴上說著:「心煩,不提他了。」可話題都在蔣同學身上打轉。
女生總是如此,口裡說著這人種種不好,心中卻是暗暗的甜著。
飯畢,熊曉苗離桌的時候,才發現隔壁桌上有支手機,拿到手上把玩。
梅嬈說:「NOKIA 6110。」
推開滑蓋,螢幕上是一對雙胞胎的照片,很小的娃娃,背靠背坐著,吮著手指,粉嫩可愛的樣子。
梅嬈說:「好可愛啊!估計是個媽媽丟的。」
熊曉苗想想還是把手機握在手上,走了出去。
梅嬈笑她:「妳盡找事,手機交給櫃檯就好了!」
熊曉苗說:「KFC的櫃檯一忙肯定忘了,人說不定有急事!」
梅嬈無奈,這熊曉苗的個性還真不是一般的強。
走著走著,電話就響了,一首英文歌,都不是兩人的鈴聲,一開始還沒反應,熊曉苗一想不對勁,立即翻了包去找,電話還好沒掛。
熊曉苗接了手機趕緊「喂」一聲。
那頭頓了一下,試探喊了句:「趙水光?」聲音淡而清雅。
熊曉苗搖頭說:「先生,你好,我叫熊曉苗,剛才在德基樓下吃飯時撿到的手機……」她blah blah講了一大堆,才反應過來那邊可能聽呆了,「喂」了一聲。
對方倒是極有涵養,說:「謝謝。我想可能是我妻子丟了手機。」
一直是平平的調子,不遠也不近,但他說「妻子」之時倒是有不可察覺的呢噥。
熊曉苗是懂愛之人的,微微笑了下。
對方又問:「妳在哪裡,可否耽誤一下?我立刻過來拿。」聲音客氣卻用的是肯定句。
熊曉苗點頭說:「好,我就在德基下邊的KFC。」
那男人說:「謝謝,麻煩。」俐落的收了線。
梅嬈問:「怎麼?是失主?」
熊曉苗苦笑:「失主的老公!」拉了梅嬈說:「走,去KFC等!」
梅嬈數落她:「妳個呆子,哪有為人辦事那麼倒楣的!」
熊曉苗傻笑,推開手機,又看到那對雙胞胎的照片,她倒是有點好奇,那男子的聲音隱約的透出種貴氣,估計是精英小白之類的,她被夏靜生訓練慣了,也不覺得有什麼了不起。
倒是這對孩子笑得無邪,粉雕玉琢,什麼樣的父母能生得出來呢?
坐在KFC裡,和梅嬈共喝一杯果汁,慢慢的期待起來。
★★★
才半杯果汁的時間,就有個穿西服的男子推門走了進來。
不是熊曉苗太聰明,而是來人一身絲光的高檔西服,正兒八經的樣子,一點都不像是來吃KFC的,倒像是正在參加什麼重要的會議。
那人氣勢極強,一走進來倒像全部的氣場都吸過去了,幸好工作日的下午KFC沒太多人,那男子眼光繞了一圈,落在熊曉苗那桌的手機上,跨了步子走過來。
不知怎麼,熊曉苗倒和梅嬈立即認認真真的站起來。
那男子走近,真的是一副極好的面容,約莫三十左右歲,有股成熟的貴氣,似細炭筆勾勒出的深邃的眼,涼薄的唇,他伸出修長的手,頷首微微一笑,說:「妳好!」
熊曉苗心裡直嘆,這人真沒辱沒他的聲音。
她剛才電話裡聽來那聲音就是極品──雖然極品男人的聲音一般都很極品,但不代表有極品聲音的男人都長得極品!
熊曉苗這樣花癡了一把,回神一看,人家的手還是懸著的,趕緊伸了手去,那男子似是習慣了,也不在意,握了一下,很快的放開。
熊曉苗也是懂外國禮節的,只覺得這男子的教養極好,輕握了立即鬆開,掌心無汗也不緊貼著對方,到底是個人物。
騰出了手後,她拿了手機遞給他,那人也不急著要,淡淡說了聲:「謝謝。」就拿出錢包來。
熊曉苗頭大,這些高貴人類就是麻煩,撿了手機這麼小的事還要給錢,擺明了算清帳,不想欠人情。
想想自己家裡貌似也有這麼個極品,有點理解,但還是擺了擺手說:「不用了,一點小事而已。」
那男子抬頭,看她確實一臉堅決,微皺了眉,一張俊臉有點冷,想想,從錢包抽出張卡片來,遞給熊曉苗,說:「這是我的聯繫卡片,以後有什麼需要幫忙的,可以打這個電話。」
梅嬈在一邊拿胳膊抵熊曉苗,熊曉苗倒也乾脆,二話不說點頭收下。即使不打電話,有帥哥的名片也是不錯的。
那人看熊曉苗收下了,淡淡笑了下,轉身就走,似是有點急事,走了兩步,倒又是那英文歌悠悠的旋律傳過來,他低頭看了電話一眼,按了鍵接了起來,「嗯」一聲的上揚。
熊曉苗巴著腦袋在後面看,那男子拉了門出去,薄唇輕啟,說了句什麼。
熊曉苗努力聽,只聽到幾個「回家」、「寫檢查」之類的詞,咧了嘴笑起來。想來要是她丟了手機,夏靜生也是會讓她不好過。
再抬頭,那男子拿了電話,走過轉角,一側身的剎那,臉竟不是那麼冷冽了,眉眼微低,側了頭貼著電話,傲然的臉部輪廓似乎柔和了不少,真是奇妙。
熊曉苗這才低頭看卡片,燙金的邊,倒不是名片,三個隸書大字「談書墨」,看得出是按原版複製上去的,蒼松的字跡很有勁道,下面一小行電話號碼。
真是個怪人!
梅嬈嘆:「熊曉苗,幸好妳撿了那電話!那男人帥得不行啊!我看到那男人的錢包是Hermès的,還是新款,我才在我同事的雜誌上看到……」blah blah說了堆,激動極了,不知道以為是遇見明星了。
熊曉苗頭疼,「這叫好人有好報,但我覺得我家小靜更帥點!」說最後一句話時,揚了下巴。
那男人是帥,但要凍死人了,她大氣都不敢出。同樣都是極品,還是她家夏靜生同志好,夏極品還幫她洗碗,沒事吵吵嘴,看,她家老公多宜人宜家啊!
梅嬈掐她:「好人個鬼!把妳解剖了,看看是什麼體制,老遇上帥哥,讓老娘這種人怎麼活啊!」
熊曉苗拿了包包去擋,知道梅嬈不是來真的,就愛和她互掐而已。
玩笑中,又想起那對雙胞胎的照片。
談書墨?
和那樣的男子在一起的,定是個神仙般的人物!
人生真奇妙,在小小的南京城居然有這麼一戶人家。不知道他們是怎麼過日子的?像她和夏靜生一樣嗎?
此時,夏靜生正坐在偌大的會議室裡討論「陽光小鎮」的建築材料競標案,臨近結束,手機開始震動起來──能這時發短信的也只有某個呆子了。他嘆了口氣,悄悄在桌子底下拿出手機。
果然是熊曉苗的短信:小靜先生,告訴你件事,我今天幫個極品撿到手機,他還給了我手機號碼!好人有好報吧!
筆擦過柔軟的紙面,他看著短信,竟能夠想像她說著這段話的語氣。嚴肅的會議似乎不那麼枯燥了,他眼角輕斂,嘴角愉悅的揚起,長桌下,長指靈活的動了起來。
發的時候突然覺得和她來到了大學時代,坐在一排排的階梯教室中,躲在桌下商量著中午吃什麼種種的話題,笑容不知不覺的擴大。
顧思遠坐在旁邊,看了個七七八八,咳了一下,不懷好意的笑著。
夏靜生抬頭,桌下踢了顧思遠一腳,檯面上一張清俊的臉卻風平浪靜。
大家正交頭接耳的討論提案,他也是懂分寸的人,伸了細長的指,握拳,低了頭,鏡片掩住垂下的眼睫,輕咳兩聲遮了笑意。
很快,他又抬了頭,彎了指節敲了敲桌面,清脆的聲音一下子引回了注意力,溫文一笑,鏡片後眸子裡卻精光畢露,很清晰卻不急不慢:「最後,大家對於這份議案……」
精英小白的定義就是,玩樂歸玩樂,什麼事情都懂得分寸,還有要立即進入狀況。
熊曉苗收到短信,樂滋滋的立即打開──
早點回家,電話刪了!
「哈!」她一下子就笑了起來。還是她家夏靜生可愛,她還沒告訴他只是張卡片而已……算了,卡片還是隨手丟放吧。
這樣笑著一抬首,正好對上迎面走來的兩個美女。
笑容來不及收,正對上人家,其中一個面無表情的轉了視線。
熊曉苗摸摸臉。唉,就是這夏靜生,她都被人認為是神經病了。
管他呢!
她拎了包包,往前走。
每一天每一天,我們都帶著自己的故事,與一個又一個的故事擦身而過。
當然,夏家的故事還在繼續。例如此刻……